|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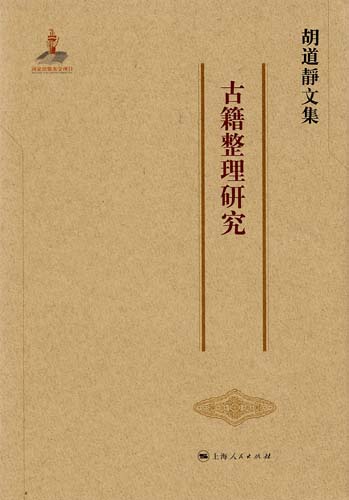 胡道静(1913-2003)先生毕生的主要职业是编辑——解放前曾任《正言报》及《中央日报》等编辑,建国后长期担任我国出版界重镇中华书局上编所及上海人民出版社的资深编辑,殚精竭虑,献身于“为他人作嫁衣”的平凡而伟大的事业。他还长期坚持业余治学,因出身名门,又转益多师,打下扎实的目录、版本、校勘、辑佚学基础,在学术研究领域广泛涉猎;在中国科技史、农史与农书、历史文献学及《道藏》、道教文化的精湛研究中均有重要建树,他执著于沈括名著《梦溪笔谈》的校证,对沈括生平的研究逾半个世纪,在海内外享有极高的学术声誉。道老学问博雅,为人谦厚,对自己学而无厌,对后学诲人不倦。他的学术成就早已享誉世界,其学术著作、治学方法果然惠泽后学、津逮学林,其道德风范、“毫不张扬的人格魅力”,更是千古楷模,令人叹为观止,当得起“先生之风,山高水长”之誉。上人社没有忘记这位德高望重的元老,在他归道山八年后,为庆贺道老百年诞辰,将道老的主要论著汇为文集刊行,成为新世纪学术界一大盛举。 胡道静(1913-2003)先生毕生的主要职业是编辑——解放前曾任《正言报》及《中央日报》等编辑,建国后长期担任我国出版界重镇中华书局上编所及上海人民出版社的资深编辑,殚精竭虑,献身于“为他人作嫁衣”的平凡而伟大的事业。他还长期坚持业余治学,因出身名门,又转益多师,打下扎实的目录、版本、校勘、辑佚学基础,在学术研究领域广泛涉猎;在中国科技史、农史与农书、历史文献学及《道藏》、道教文化的精湛研究中均有重要建树,他执著于沈括名著《梦溪笔谈》的校证,对沈括生平的研究逾半个世纪,在海内外享有极高的学术声誉。道老学问博雅,为人谦厚,对自己学而无厌,对后学诲人不倦。他的学术成就早已享誉世界,其学术著作、治学方法果然惠泽后学、津逮学林,其道德风范、“毫不张扬的人格魅力”,更是千古楷模,令人叹为观止,当得起“先生之风,山高水长”之誉。上人社没有忘记这位德高望重的元老,在他归道山八年后,为庆贺道老百年诞辰,将道老的主要论著汇为文集刊行,成为新世纪学术界一大盛举。
令人啧啧称奇的是:道老一家三代(其先公怀琛太先生、哲嗣小静学长)均献身于沪上出版界,并创造了非凡的业绩。道老的学术生涯如从1930年上大学时编纂“万有文库”本《农政全书》算起,到2003年为《海外新发现〈永乐大典〉十七卷》作序止,凡七十余年,他又长期担任国务院古籍整理规划小组成员、顾问,是实至名归享有世界声誉的权威学者,而且是主要靠业余治学而成名的学界泰斗,兼又人生经历极为坎坷,尤为难能可贵,更令人肃然起敬。
1984年,我赴上海师院(今上师大)参加程应镠先生指导的硕士研究生考试复试;行前承道老解放前上海《中央日报》社同事程玉西先生修书荐介,有幸拜识道老。当时他住四平路寓所,因小静学长“文革”中“炮打张春桥”而父子蒙冤,入狱九年。道老平反后,又大病一场,时刚恢复健康不久。初见前贤,不免拘谨,但道老在书房“海隅室”亲自为我沏茶,又问起程老近况。我答称:程老现任盱眙县政协副主席,已落实政策。这位百岁老人至今仍健在,在盱眙随儿孙安享晚年。今仍能电话中回答我的请教说:“道静1948年在《正言报》工作,因该报内部矛盾而离职,经我(程老)介绍进《中央日报》工作,任副主编,当时我任主编。”这一回忆,可补道老生平简历之阙。程老亦非等闲之辈,当年作为新闻记者的代表,与陆诒等一起成为宋庆龄、蔡元培、杨铨(杏佛)发起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成员(成员名单今存上海鲁迅博物馆)。该会上海会员还有林语堂、王云五、邹韬奋、胡愈之、鲁迅、茅盾、郁达夫、叶绍钧、全增嘏、王造时等名人。故程老亦在“文革”中吃尽苦头,所幸他为人低调,又隐居在县城,故逃过一劫。道老则在1932年“一·二八事变”中,两大屋藏书灰飞烟灭。抗战中逃难途中九死一生,当时桂林报纸误报道老遇日机轰炸遇难,原上海通志馆主持柳亚子先生曾写下悼文。孰料一生追求光明真理进步的道老,在“文革”中蒙受飞来横祸。长期积累的大量文稿(仅《中国农书总录》就逾百万言),扫地以尽,片纸无存。劫后余生的道老,在人生的最后二十年中,仍有老骥伏枥的壮志雄心,在农学和道学及古代典籍的研究中再创辉煌。我身为立志在学术上有所作为的后学,从道老百折不挠的经历中深受教益。当时,他书室中摆满盛皮鞋的空盒,我好奇地问道老有何用处,道老答云:步入老年,身心备受摧残,记忆力急剧下降,治学当从目录版本始,要从做卡片积累做起。斗室陋窄,以皮鞋盒乃代替抽屉,便于分类存放卡片。他又和我讲起,宋人李焘为写《长编》置两大橱,各二十抽屉,凡四十匣,每匣盛数年的史事考证材料,历时四十年之久,北宋九朝一百六十八年的《长编》就是如此编写而成的。治学除了下苦工夫,还得讲究方法,才能有事半功倍之效。道老又赐我发表未久的大作《类书的源流和作用》一文。他指出:“类书的作用首先是可用以校勘和辑佚”,这对我后来茶书汇编与校证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如《茶经》的宋本早已亡佚。今存最早版本用南宋末收入《百川学海》中的残本《茶经》,但在唐宋的类书、方志、别集的诗文注中还存在大量引用《茶经》的佚文。笔者在长达二十余年的时间中,正是依赖广搜博采,才改正了今本《茶经》上百处衍误讹夺,整理出一个最接近于陆羽《茶经》的新本。五代毛文锡的《茶谱》是已佚的重要茶书,笔者遵循道老的教诲,从类书及四部书中从事辑佚,也取得了满意的收获,被公认为“迄今最备最佳的辑本”。道老重视目录校勘版本学的教诲令我终生受益。初识道老,就从他语重心长的教诲中,如沐春风,备受教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