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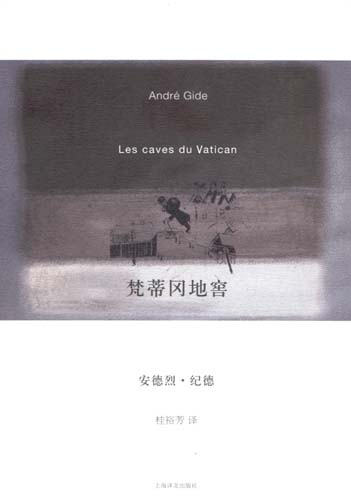 我一直觉得,安德烈·纪德是一个很矛盾的人,他内心的冲突感太强烈。神性与人性,情感与理智,传统与个性这些在普通人身上和平共处的原则,在他身上却像浸透了雨水的胶带纸,始终难以粘连到一起,以至于有时候他的精神明明已经飞升上天,却因为沉重肉身的羁绊不得不被拉回大地。 我一直觉得,安德烈·纪德是一个很矛盾的人,他内心的冲突感太强烈。神性与人性,情感与理智,传统与个性这些在普通人身上和平共处的原则,在他身上却像浸透了雨水的胶带纸,始终难以粘连到一起,以至于有时候他的精神明明已经飞升上天,却因为沉重肉身的羁绊不得不被拉回大地。
继承了法国艺术一贯的传统,纪德也偏爱走极端。在他的作品中人物不是太过孱弱就是太过刚强,呈现出一种鲜明而怪异的对立。
从《背德者》、《窄门》到《梵蒂冈地窖》,尽管文风变异,这一内在的紧张感却从未改变。在前两本书中,纪德通过设置人物精神上的对立来制造这种冲突,而到了《梵蒂冈地窖》——这本被他称为“傻剧”的作品,冲突却是以主人公拉夫卡迪奥的内在世界来呈现的。
纪德笔下的这位年轻人,习惯于用鄙夷的眼神看待自己周围的人事,特立独行却又渴望被认同,相信人间真情却爱表现得玩世不恭,最终鄙弃世俗的道德转而信奉一套极端唯心的自由行为哲学:为了证实善恶有时并非系于人类逐利的动机,他可以舍身冲进大火救人,也可以冷酷无情地将无辜者推下火车杀害。
质疑拉夫卡迪奥是否真实存在没有任何意义,重要的是,通过这个人物,纪德实质上为人类设置了一个难以逾越的生命困境:自我救赎之不可能。
自康德悬置真理,外在规约土崩瓦解,人类孤苦无依,只能仰仗头顶的星空和内心的道德律,但是浪漫主义思潮和此后掀起的尼采哲学,更是进一步解构了科学和良心给人类带来的存在感,回归传统之不可能迫使强者走向为自己立法的道路,而这一法则需以弃置基督教孱弱的道德传统为代价。就如尼采所说:自由的人是不道德的,因为在所有事情中他决心依赖自己而不依赖传统。
当尼采试图用生命意志为自己立法,却忽略了抽离理性的世界本身是流变不居的。
善恶是非,规则既然全由自己厘定,就很难保证前后一致。看似无动机的事物中却隐含着因果报应,当结尾处,拉夫卡迪奥需要面对爱人的眼泪和赎罪自首的两难境地时,他不能不承认自己从头到尾错了:为了坚守那个稳固的、本质性的自我,证明自己是生活的主宰者,他必须去坦白自首;可是坚守自我的代价却是,毁掉爱人和自己的幸福,让自利者获得机遇。赎清了一桩罪,却要犯下另一桩罪。
在纪德看来,既然投身于茫茫的时间之流,我们就随时面临着被时间改变的危险,一个人道德标准的前后不一才是生活的常态,人皆有两面性,与其掩饰这种两面性,倒不如将它发挥到极致才淋漓畅快。
人是因为有了自我认识才开始学会忠于自我,而那个稳固的自我的核心,恰恰是僵化而可怕的,人们生来存在于矛盾中而不自知。既然连终极的、本质的自我都是一个虚空,要谈救赎显然是可笑的。或许正因为如此他才会说:我所讨厌的是某种坚定的一致,某种忠于自己的意志,以及对于自我矛盾的恐惧。(《地粮》p.216)
拉夫卡迪奥是纪德从《背德者》、《窄门》以来的道德回归,从解构尼采超人哲学开始,纪德反思了早年自己对于欲望所抱持的无所顾忌的赞美态度。
自此,纪德终于将自己小说的议题转向了他的幸福伦理学:为自己立法的哲学诚然是可行的,但对于真正的强者来说,自我救赎的可能性并不在臣服于强大的生命意志,而是最终学会随心所欲不逾矩,逾越常规并非对自由意志的肯定,却将是一种慢性的自我伤害。尽管上帝已死,人类无依无靠,人仍然需要学会对自己负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