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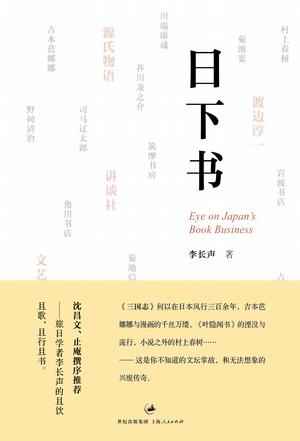 李长声的文字,过去常常在《读书》杂志上见到,他早就是我心目中写日本读书界动态的权威。我对日本人的文字有好感,最早接触的日本人的文字是小林多喜二的小说,那是还在“文革”时期。后来像很多中国读者一样热爱过川端康成。不过,印象最深的是安永一写的日本围棋史话,真想找来再读,不知道还能不能找回过去那种激动人心的感觉。“80后”的一代对日本的了解程度超过我们,他们是看着日本的动漫长大的,有人因此甚至学会了一点日语……我对李长声的文字一向留意,《日下书》到手,发现不少文章都是熟悉的。 李长声的文字,过去常常在《读书》杂志上见到,他早就是我心目中写日本读书界动态的权威。我对日本人的文字有好感,最早接触的日本人的文字是小林多喜二的小说,那是还在“文革”时期。后来像很多中国读者一样热爱过川端康成。不过,印象最深的是安永一写的日本围棋史话,真想找来再读,不知道还能不能找回过去那种激动人心的感觉。“80后”的一代对日本的了解程度超过我们,他们是看着日本的动漫长大的,有人因此甚至学会了一点日语……我对李长声的文字一向留意,《日下书》到手,发现不少文章都是熟悉的。
日本是书的大国——居然四千多家出版社。日本的文盲几乎等于零——英美两国也无法彻底扫盲。日本的阅读人口很可能比中国多——以一年读五本书为有效阅读人口计算,中国的阅读人口可能非常之少。很多在日本玩过的那些“书游戏”——评奖、讲座、签售、对话等等——在我们这里要迟到十年甚至数十年才慢慢展开。有些现象现在是彼此彼此了——比如说,在日本现在也是养生类的书热销,在我们这里也是如此。其实一切跟书有关的人——读书的、写书的、卖书的——都应该重视日本书世界的“情报”——并非只有某些特别部门才对情报感兴趣,一切资讯皆情报也,八卦其实也是情报之一种也——因为他们先发一步,我们如果及时了解,就能够洞悉出版业的先机。
因此,李长声这样情报意味很浓的书是蕴藏着“商机”的。比如说,改写经典在日本也是热门,像是吉川英治的《三国志》就比《三国演义》来得有影响,非常畅销。为什么呢?现代人要用现代人的口味来活化古典,才能够读得津津有味,于是乎一切古典书也因此都是现代书。我们这里的当年明月改写明史,于丹改写《论语》,都成为一时的畅销书。中国的古典经典还很多,不妨一一改写之,用经典的酒瓶子,装今天的读者心目中的新酒,这对作者来说不是商机吗?
对搞编辑出版的人来说,期刊曾经是赚钱的买卖,日本过去就是刊物比书籍赚钱,中国的情况似乎也是这样。光是一个讲谈社2006年就出版了106种杂志。日本杂志的两大宗是漫画杂志和女性杂志。漫画杂志不靠广告,靠发行量大。女性杂志则主要靠化妆品广告。我曾经认为,随着电子媒体的出现,纸媒杂志可能江河日下了。但现在看来未必是这样。窃以为日本漫画书的流行跟地铁关系很大,坐地铁的时间长,看文字书累人,于是乎漫画就大行其道了。有鉴于此,我们不难想见商机之所在——比如,包括深圳在内的很多城市即将进入地铁之城,乘坐地铁的人将会越来越多。在地铁上拿笔记本电脑看杂志很不方便吧。不如一本短小轻薄的杂志漫画之类在手,看完就扔掉。这是出版的商机。
如果说日本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那么,出版业的广告还有非常大的开拓空间。在日本,各大报纸的头版常常刊登出版广告——这确实是匪夷所思。我们的报纸头版一般都是房地产广告和汽车广告。日本的广告费用中,第一位的是娱乐,第二位的是教育,第三位的是出版业。现在做出版的人舍不得花钱做广告,很多有机会成为畅销书的书都没有畅销。当然,这跟我们的阅读有效人口不多有一定的关联,但未必完全如此,我们犹记得当年一本《学习的革命》畅销,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大做广告。虽然有人指出做广告的目的是为了宣传那家公司,但无论如何,用广告的方式推销书这样的商品,应该是可行的。
不过,我之读《日下书》,最喜欢的还是闪烁在书间的那些琐屑和八卦。比如说旧书铺:“女性向来不上旧书铺,嫌脏。人类女性化……”,人类确实在女性化;日本公司里,大家用渡边淳一的小说进行“纸上性交”,于是渡边的小说被称之为“卫生纸小说”;日本的武士道小说代表首推《叶隐》,叶隐的意思是隐藏在树叶之间,这个意象有意思;李长声说中国作家缺少自我厌恶,自我感觉良好,都活得那么滋润,所以出不了什么大家;日本最近三十年来,编辑工资涨了二十倍,但稿费仅提升了五倍;小林一博说书有三大罪:占用人的时间,迷惑人,吃掉森林;见城彻做编辑结交了很多朋友,朋友是怎么结交的呢?喝酒。见城彻出版《编辑病》一书,献给他一生任性爱恋过的9个女性;有人说,想了解人性,读一流的作品,想了解国民性,读二流的作品;日本人喜欢出全集,往往是出版社的救命法宝;日本的文学奖竟然有450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