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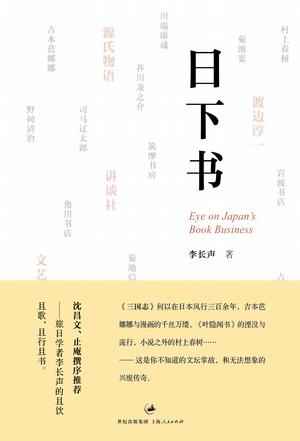 “书之书”,即以书为主角的书。由爱书人所写,多书里书外的把玩与探求。一个书籍写作与阅读悠久的传统,每年都有人接续。读它们,会觉得有些作者就像侦探,在倾力挖掘一本书背后的秘史;而有一些,则像在与原书扮鬼脸,常常拿些鼎鼎大名的名著做戏仿,要的是那种机智有趣的误读。还有一些,生生造一些虚拟之书,让主人公费力去寻找,增加一些故事的悬念;另外一些,则把书当下酒料,时不时就拿出来嚼一嚼。 “书之书”,即以书为主角的书。由爱书人所写,多书里书外的把玩与探求。一个书籍写作与阅读悠久的传统,每年都有人接续。读它们,会觉得有些作者就像侦探,在倾力挖掘一本书背后的秘史;而有一些,则像在与原书扮鬼脸,常常拿些鼎鼎大名的名著做戏仿,要的是那种机智有趣的误读。还有一些,生生造一些虚拟之书,让主人公费力去寻找,增加一些故事的悬念;另外一些,则把书当下酒料,时不时就拿出来嚼一嚼。
不管什么样的姿态,他们都是书籍热情而隐秘的传递者,他们深知,“故事想要被阅读,这就是它们拼命从它们的世界来到我们的世界的原因。”这里的故事,完全可以替换成书籍。是书籍从落地那一刹那就有的渴望。而这些爱书人读懂了它们,并把它们做了自己的书写探求对象。一个书的内部世界由此被打开,那也是一个与我们的渴望、恐惧、隐秘、好奇相关的世界。
为对抗恐惧而寻找的书
《失物之书》 (爱尔兰)约翰·康诺莉著、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这是一个魔幻书,也是一本成长书。从德国作家柯奈利亚·芳珂的《墨水心》到爱尔兰作家这本《失物之书》,你可以看到西方的作家以书为主角,总是毫无障碍地就把书与现实之间的坚墙打破。柯奈利亚运用的是朗读的魔法——一个有神力的人朗读到书中的哪一页,就可以让书中人跳到现实中来,但也往往容易让现实中一个人(很可能是朗读者至亲的人)落入书中也落入危险中。于是就一定有一番紧张而冒险的营救,必要时,还会把原书作者搬过来做救兵,来一场现实人物与虚拟人物的较量。
而在《失物之书》中,作者则是用了这样一个说辞:“一些古老的故事,会得到一种独立于它们占据的书页之外的存在。古老的传说与我们平行并存,也因此,隔绝两个世界的那堵墙变得薄而脆,于是两个世界开始相互混杂在一起。”以这个说法搭起平台,故事中的小男孩就可以经历一种虚构中的历险了。历险的原因说来特别令人心疼,男孩子为什么要不远万里寻找一本《失物之书》,只因他失去了妈妈,又不接受父亲的新爱,更不愿意看到他们的孩子乔治出生,夺走了他们对他的爱。他想恢复原有的幸福生活的愿望如此强烈,以至于听到了书的窃窃私语。正是这神秘声音的召唤,让他深入丛林,遇到扭曲人、森林人,还有一系列的凶险之事,最后抵达国王的城堡。他被告知,能让生活回到以往的《失物之书》就在这里,结果发现,书的作者就是那个孤独虚弱的国王,他也曾经是个孩子,却因为恐惧、嫉妒而远离亲人,并且让自己同父异母的小妹妹也成为牺牲品。这俨然就是男孩自己曾经的内心写照。不过,在经历了这漫长的寻找与历险之后,他早已战胜了内心的怯懦与妒忌,他学会了信任、体谅、勇敢的承担,也因此完成了从男孩子到男人的转变。
这本名叫《失物之书》的书出现在故事中,充其量只是个隐身的道具,但却构成了故事最大的悬念。虽然故事的中途依旧无法避免许多西方故事的俗套,但是有这种内在牵引,它依然算得上引人入胜,因为它最大限度地替我们找回了童年的感觉——那时我们多么相信,故事并不只是故事,它一定是另一种生活,它隐藏着真相又诱惑我们寻找,它在和我们躲猫猫。而幸运的孩子,是可以被邀请到故事中,成为其中的角色。
现在这个幻觉已经不存在,我们也无可救药地长大了。
谁在书的背后躲猫猫?
《多米尼克·奥莉:藏在〈O的故事〉背后的女人》 (法)安吉·大卫著、新星出版社出版
《O的故事》是一本情色书,后来被改编成电影。电影的精神意旨并不能和书画等号,因为这本书除了情色还有其他。许许多多的秘密就潜藏在这个叫多米尼克·奥莉的女人身上,她是《O的故事》的真正作者,她同时还有另外的身份:纯文学的翻译家、评论家,法国伽马出版社审稿委员会唯一的女审稿人。可以说,她生活在一个严肃的纯文学圈中,却秘而不宣地写了这么一本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书。她的情人、也是纯文学圈中的一员的让·波朗,也是这本书的知情者,但他与她共同保守了这个秘密。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这秘密由她亲自道出。当然,她的秘密还不止这些。
法国文学研究者安吉·大卫用一种可敬的方式(而非一种津津乐道的猎奇式)探究这位神秘作家的一生,从而赋予这本传记文学庄重严谨的面貌。它在向你展现一个持续了几十年的禁忌的游戏的同时,也让书与作者,作者与他人,文学与现实都在禁忌中展开它的无限丰富性与不可言说性。它宽广的视野甚至把当时的法国文学界文化界都扫描了进去,你也可以说,在谈论《O的故事》背后的女人时,法国那段时期最重要的文化议题也都被一网打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