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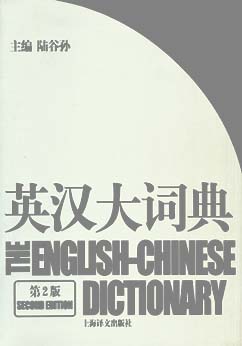 我从大四起受教于陆谷孙老师,在陆师门下攻读“双语辞典编纂”博士学位。期间正值《英汉大词典》修订。辞典编纂,在他人看来可能枯燥乏味至极,但陆师一直保持着一种“找乐子”的心态。 我从大四起受教于陆谷孙老师,在陆师门下攻读“双语辞典编纂”博士学位。期间正值《英汉大词典》修订。辞典编纂,在他人看来可能枯燥乏味至极,但陆师一直保持着一种“找乐子”的心态。
诚然,辞典修订中是要“抠字眼”,一行行小字要一一校对,一个个释义要反复斟酌,一本本参考书在案头堆成了小山。忙乎半天,读者从词典得益纵有十分之八九,那一两分的错误或缺陷,一被抓获,照样可把你批个体无完肤。所以就过程论,编词典是“delays + deficits”(延宕加赤字);就结果论,是“defaults + deficiencies”(错失加疏漏)。是陆师教会了我们怎样在“无害的苦役”中自找乐趣。遥想“文革”年代,某些人出于将思想“毒害”控制在最小范围内的考虑,将他调离教学岗位,“发配”至词典编纂组。陆师苦中作乐,与“工宣队”迂回周旋,悄悄地将“毒草”类词条、例句插入当年的《新英汉词典》中,以至于词典出版之日,西方世界震惊不已——在“文斗武斗”的中国,居然还有人用非母语者特有的敏锐,密切跟踪英语国家的用语变化!
修订中的一个乐趣,就是景仰前辈在释义、翻译中体现出来的巧思妙想。舶来运动饮料“Gatorade”被译为“给他力”,音意跃然纸上。相比之下,商家所采用的“佳得乐”牌号黯然失色。当然,在这政治正确的年代,运动饮料只给“他”力不给“她”力,恐怕是厂家不能承受之重。
记得在修订期间,陆师曾要我找一下“Jacuzzi”一词的通用译法。我在网上搜索,也去了有此类设施的会馆实地侦察,发现是“按摩浴缸”。陆师却想出了一个惟妙惟肖的译法——“惬可适”,是不是很能反映人泡在暖洋洋的按摩浴缸中那种快意?
一本大词典,洋洋洒洒二十余万条,数百万言,真可谓“上知天文,下晓地理”。而修订中的第二种乐趣,就是我们学会了对世界始终抱有好奇心,语言文学以外的东西都愿意学一点。陆师是我们绝好的楷模。因特网还不是很普及的时候,陆师已经开始“冲浪”了;手机一流行,陆师就成了“拇指一族”。记得一次登门,陆师在纸上写了“shaping”一词问我何意。碰巧我这人爱赶时髦,倒是知道它是一种刚刚传入中国大陆的起源于俄罗斯的一种健身运动(那时瑜伽、跆拳道、踏板操、拉丁舞、成人芭蕾这些项目可还没有兴起),音译成“舍宾”。原来这道题陆师考了不少人,答对的还真不多。
对世界的好奇不仅体现于对流行语的敏感,也体现在对书本的渴求上。陆师一直在复旦外文院系大会上强调多读书的重要性,要求教师们至少每年读三十本书。他自己更是手不释卷,从游记读到传记,从中文读到英文,从古文读到时文。
受陆师的影响,我们几个同门师兄弟妹多少都有点“不务正业”。有的会写剧本,有的跑到国外学了“神学”,有的精通电脑,有的打一手好篮球,有的写一笔好古文。而我呢,也借着在外做同传口译的机会,政治、金融、科技、艺术都见识一点,还能趁机收集一些各行各业的用语。记得有次做了一个非开挖技术会议的口译,学到把“U-tube”译作“三通”,而《英汉大词典》里只有“U型管”一意。陆师得知后,当即决定增补。
陆师在《英汉大词典》前言中写道,有志于词典编纂的“学人会从单调、烦琐、繁重、艰辛的劳动中发掘乐趣,寻求报偿。乐趣在于遨游英语语词的海洋,报偿在于翱翔英语文化的天地。”这乐趣我也多少领略了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