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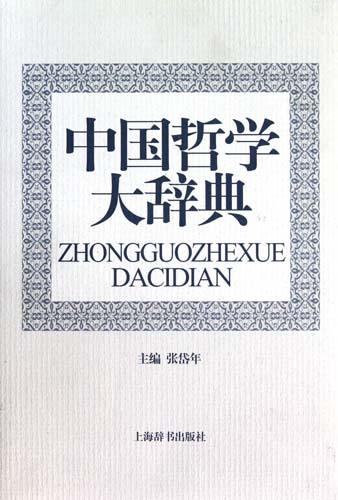 ●如今,出版界不乏一些片面认知:陷于出版滞涨、供过于求的书市,出版文化建设的政绩仍是出版产值的排名及每年20%、30%乃至50%的增长指标。●建设出版文化高地,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有一个厚积薄发的长期积累过程。 ●如今,出版界不乏一些片面认知:陷于出版滞涨、供过于求的书市,出版文化建设的政绩仍是出版产值的排名及每年20%、30%乃至50%的增长指标。●建设出版文化高地,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有一个厚积薄发的长期积累过程。
●多元出版、轻松阅读当然也是一种文化消费需求,但热衷风水、占卦、盗墓、穿越、戏说、伪保健、明星隐私,以此吸引读者眼球,不应是出版人所为。
吴士余:资深出版人,上海市出版协会顾问。著有《中国小说美学论稿》、《中国古典小说文学叙事》、《守望理性》、《再望理性》等。
建设国际文化大都市的口号又响起来了。四年前,新闻出版局长孙颙交给笔者一项任务:以“国际文化大都市”为题,策划一套能体现上海出版文化影响力的出版工程。受命之际,旋即邀请了近十位出版社社长、总编组成课题组,并征集上海高校近百位教授、领军学者的意见,鏖战数月,做出二份课题报告:一是《构造与时俱进的出版文化高地》,对近十年来上海出版作总体评估,分析上海出版资源的潜力及可持续发展的优势,梳理出版瓶颈的结症与突围方向,总结优秀出版工程的运作模式及其可资鉴的经验;二是《建设上海文化大都市出版工程》选题方案供专家、领导论证,方案设计出版项目约23项,925卷(种),总投入资金约5700多万元。选题涉及上海大都市文化探索、中国历史文化典籍整理、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研究、科学史和中西文化交流等。不少选题纳入全球化的视野,其学术水准处于全国专业理论的前沿。课题报告得到上级领导的赞赏。在等待高层审批之际,孙颙被调任他职,方案也就束之高阁。一晃数年,如今口号重提,颇有些感慨,也值得出版人的自省。
出版文化的高地建设,需要出版人的理性和坚守。口号与纲领能给人以鼓舞和信心,但作为出版文化建设的实践者,出版人注重的应是精神的凝聚和脚踏实地的行动自觉。如今,出版界不乏一些片面认知:陷于出版滞涨、供过于求的书市,出版文化建设的政绩仍是出版产值的排名及每年20%、30%乃至50%的增长指标。有悖于出版生产规律的高歌猛进,趋势附利的媒体效应,短视的价值诉求,其后果难免是来回折腾,昔日的假、大、空之教训犹记在耳。老出版家巢峰主政上海辞书出版社坚守四十余年,他的出版精神就是毕其一生献身于《辞海》。除十年修一书,还策划出版《哲学大辞典》、《历史大辞典》、《文学大辞典》、《宗教大辞典》、《军事大辞典》等数十部专业辞书,开拓了中国分科辞书的专业化、系列化的出版路径,使上海的辞书类工具书成为全国专业出版的风向标。巢峰先生并没有因“政绩”、“仕途”诉求偏离他对中国出版业的理念。这种执着、坚守、奉献的出版精神就是一种文化,也是当下应提倡的出版人文化。建设出版文化高地,首要的是锤炼、发扬这种出版人的文化精神。
建设出版文化高地,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有一个厚积薄发的长期积累过程。近三十年来,上海的一些重大出版工程,无不是几代出版人精心锤打和努力耕耘的结果。标志性的《辞海》、《英汉大词典》、《汉语大词典》、《新文学大系》、《十万个为什么》、《本草纲目》等莫不如此。希冀当年播种、当年收获的出版工程是难以达到质量上臻的目标的。重大出版工程往往是专家、学者、出版人精心论证、策划而成,决非心血来潮的一时之动。迎上、唯上、不务实,热衷自我包装,造势炒作的出版行为,往往是以折腾而告终。因此,出版人承传前辈出版人的经验和传统,应是不可或缺的文化品质。上海古籍出版社在中华文化典籍整理、研究的出版领域,之所以能保持数十年的强势和品牌,就在于对前辈出版精神的承传和发扬,出版强势、科学发展不可能产生于出版文化精神的断裂之中。
出版文化建设靠的是内涵的支撑。当下出版业走向市场的路径并非有错,但切实要防止无为而治带来的娱乐化、低俗化的出版倾向。多元出版、轻松阅读当然也是一种文化消费需求,但热衷风水、占卦、盗墓、穿越、戏说、伪保健、明星隐私,以此吸引读者眼球,不应是出版人所为。出版文化的主流是宣扬、承传中国的文化精神,延续中华文明,文化的价值诉求应与国际文化大都市的形象相匹配,没有文化精神的出版只能是一个灵魂苍白的躯壳。面对图书出版的娱乐化、低俗化倾向,也需要出版人的自省,需要提升对文化内涵的认识、理解和自觉。出版人是从事净化灵魂、延续文明的事业,若以为追逐、搏弈利益为唯一准则就能做大做强,难免是舍本求末,建设文化强国终究会成为一句高调的空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