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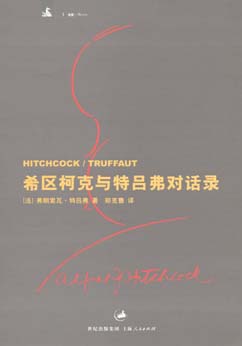 在阅读这本《希区柯克与特吕弗对话录》之前,很难说我对希区柯克有什么明确的印象。尽管刚刚翻译完了齐泽克主编的那本可谓“希区柯克迷宝典”的《不敢问希区柯克的,就问拉康吧》,可自己通览影片的心愿,因为种种原因,还处在无限期延搁的过程中。毕竟说到底,希区柯克在电影大师的万神殿中,终归是个“二流”的位置。 在阅读这本《希区柯克与特吕弗对话录》之前,很难说我对希区柯克有什么明确的印象。尽管刚刚翻译完了齐泽克主编的那本可谓“希区柯克迷宝典”的《不敢问希区柯克的,就问拉康吧》,可自己通览影片的心愿,因为种种原因,还处在无限期延搁的过程中。毕竟说到底,希区柯克在电影大师的万神殿中,终归是个“二流”的位置。
看完这本书,我想要说,希区柯克的“二流”,几乎就是他命该如此。“一个电影艺术家没有什么可说的,他要表现”,他这样说;“电影变成了抽象艺术”,特吕弗这样仰慕地总结着。可问题在于,无论当今的哪种文化语境中,不“立言”,没有语言文字的表达和记录,没有故事和寓意,就没有价值场中的位置。一个不关心人物的性格和心理,不关心故事的真实性和逻辑,只关心情节进展的速率和斜率,以及“用摄影机迷惑观众”的成就感的人,是难以获得最高肯定的。
而就是在这里,希区柯克让我想到了毕加索,这个20世纪难以评断的绘画大师。人们绕不开他,他的绘画屡次在拍卖场上爆出天价(就像希区柯克的影片屡次制造出票房奇迹),可又不得不指出,尤其在晚年,他毫无顾忌地重复着自己熟悉的题材,展示随心所欲的造型能力的欲望远胜于完成一幅作品的“任务”(在克鲁佐的影片《毕加索的秘密》中,最迷人的就是毕加索笔触涂抹之间不停地改变画面“形象”的能力,近乎奇迹)。总之,这也是一个视觉性的大脑,他仅仅关心绘画自身,超越了所有的叙事性或道德性考量。在这些方面,我想他们二人会是惺惺相惜的。
从这本书中我们发现,希区柯克是难得地执著于并信任于电影的。他从16岁开始就时刻准备着进入电影界,一旦得到了机会,又把自己工科学生对技术的激情贯穿其中。从而,在他力量所及的范围内,他总是尽可能精确地掌控电影摄制的全过程。这是一个彻底的“作者”,在默片时代,他说自己在努力“以纯粹视觉的方式进行表达”;到了有声电影中,他说重要的是“影片各部分的组合、摄影、录音、所有纯技术的东西”。总之,不是题材和人物,是纯电影在塑造悬疑,使观众激动。可以想象,这种执著不可能永远成功,希区柯克经历了多次沉浮,一生处在失败与成功的反复轮回之中,但他相信自己,他对特吕弗说,“才能总是在那里”,等待着新机会的出现。
在希区柯克的影片中,存在着很多奇妙的悖谬,这是我在这本书中有趣的收获。关于麦格芬的空洞性,在希区柯克眼中,这是一个一贯的形式简化原则或曰叙事经济学,如无必要,勿增实体。毕竟,你设计一个具体可感的阴谋,就要让它充分发展已达到逻辑的结果,这是叙事的必要,但太麻烦了。何不用托辞一笔带过呢?但另一方面,希区柯克又是细节的狂人,他永远有着要“填满画面”的顽念(这又像毕加索,他无法忍受一张空白的画布)。一些场景中充满了微妙的细节,观众可能根本注意不到,但他兴致勃勃地设计,因为他坚信这些细节在影片整体中、在观众心理中是起过作用的。而且它们可以保证在反复观看中有新发现,使影片不会过时。归根到底,无论是简洁还是繁复,没有什么是多余的。这简直可以说是希区柯克的信仰了。
还有陈腐与新奇。希区柯克的场景陈旧、人物平面,这是批评家的老生常谈了。他自己也说,在瑞士,就要有巧克力和湖泊;在荷兰,是郁金香和风车;意大利人,就要是虔诚的天主教徒。这其实还是经济原则,最大限度地使地方元素戏剧化,使人物形象的建立简洁化。但就是在这种“明信片风景”的堆积中,出现了他最生动复杂的影片,英国时期的《三十九级台阶》和美国时期的《西北偏北》。与其徒劳地说清楚它们的故事,不如说,这是“空间穿越”影片,主人公在“麦格芬”的驱动下,走遍英国或美国的典型风景。在影片中,情节环环相扣,但难以言传。有一个段子,《西北偏北》的拍摄中加里·格兰特终于忍不住来找导演:我们都拍了三分之一的影片了,发生了各种各样的事,我却一点儿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关键就在此,影片发展到三分之一时,主人公确实还“一点儿也不明白”自身身上发生了什么。观众呢,他们大概明白,但这里的麦格芬彻底空洞,它是“国家机密”。
还像毕加索,希区柯克的一生贯穿着技术激情和实验欲望。在《夺魂索》,他进行了胶片时期唯一一次无剪辑90分钟长镜头;在《欲海惊魂》,他冒天下之大不韪地用谎言充满闪回;在《后窗》,他清楚地知道自己在制作纯粹讲电影技术的影片;在《惊魂记》,他对用摄影机迷惑观众的创造性运动沾沾自喜;在《群鸟》,他系统地使用了电子合成音响。听着希区柯克在特吕弗的诱导下讲述这些历史,总是一件有趣的事情。何况还有这个人的幽默感,以及深入骨髓的精神分析意义上的反常,就像他自己说的,“我从来不能与平常的东西相协调,我在寻常的东西中向来感到不自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