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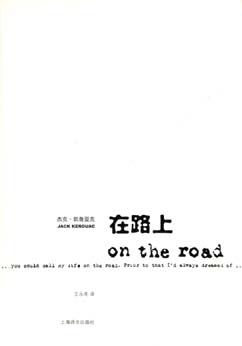 上海译文出版社近日推出了美国“垮掉的一代”的文学代表作《在路上》,这已经是该书的第四个中文简体字版本了。记者为此采访了上海译文出版社的总编助理赵武平先生。 上海译文出版社近日推出了美国“垮掉的一代”的文学代表作《在路上》,这已经是该书的第四个中文简体字版本了。记者为此采访了上海译文出版社的总编助理赵武平先生。
周报:《在路上》一书从初版至今已将近50年,请问上海译文出版社选择现在再版这本书是出于什么考虑?
赵武平:自从1957年问世以来,尽管这部自传体小说引起的社会争议从来都没有停息,但也从来没有缺少过一代又一代对之迷恋不已的青年读者。
“垮掉派”文人是二战之后质疑和否定传统文化价值观的最重要的力量,他们对主流文化的态度和观点影响了后世的人们对文化的理解。这批作家玩世不恭,笃信自由主义;创作大多自发,甚至非常混乱;作品备受争议,不遵守传统创作常规,结构和形式杂乱无章,语言粗糙、粗鄙,对当代西方文化影响深远,被公认为西方第一支真正意义上的后现代“亚文化”。
上海译文出版社向来以引进推出在世界各国文化领域对人类思想产生过重大影响的经典文学作品为己任,二三十年来持续出版了美国各个历史时期占据重要地位的文学名著,近年仍在致力于介绍纳博科夫、菲力普·罗思和厄普代克等当代美国重要文学名家的代表之作。凯鲁亚克的《在路上》作为美国后现代文学流派的典范作品,当然也就成为必须出版的对象。
从国内需求来说,在不同历史时期出版的《在路上》,由于政治、社会和思想意识的限制,或者由于译者学术观念以及研究水平的差别,旧的译本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缺陷,新一代读者期望能够看到完整、规范和权威的新译本,这也是我们特别邀请著名翻译家、新华社高级编辑王永年先生重译此书的起因。
周报:与以前的译本相比,上海译文出版社推出的新版本有什么不同?
赵武平:最大的不同,是版本的权威性。这一次采用的是1991年企鹅出版公司的定本。译者严格按照权威原著,逐字逐句翻译,原文中的异体字,有所强调的内容,包括作者原文引用的各种外文,这个译本都有明确标志。
这个版本,是作者凯鲁亚克的挚友安·查特斯,根据不同版本校勘后,编定的权威版本。新的译本,同时附录了“跨掉的一代”专家查特斯为《在路上》所撰写的长篇学术导言,《在路上》打字稿的部分影印样以及凯鲁亚克的多幅水彩画作,还有凯鲁亚克等“跨掉的一代”同时期作家的生活照片。
此外,新译本校订了以前译本的错误和遗漏的语句。对一些作者特别创造的术语,还以注释的方式,特别予以说明和解释。这不仅给读者在阅读上提供方便,同时也提供了一种阅读的愉悦。
周报:你认为现在重读《在路上》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新的启发?
赵武平:美国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是经济蓬勃发展时期,很多正统的社会人士,追求丰富的物质回报,所使用的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很多追求精神自由的青年人开始出现心理危机,流于寻找生活和精神的突破,但是限于环境的压迫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有所作为。因此,凯鲁亚克和金斯堡等叛逆型的“跨掉一代”作家作品的出现,给了苦闷的青年人心灵的自由指向标,受到了极大的欢迎。对比我们所处的时代,其实不是没有近似情况的。
凯鲁亚克写小说时,本意并不想非难战后美国的自满情绪和歌舞升平的景象,但是他创作的书预示了国内思想意识的变化。威廉·布勒斯指出:“1957年,《在路上》出版后,美国售出了亿万条牛仔裤和百万台煮咖啡机,并且促使无数青年人踏上了漫游之路。
当然,有一部分要归因于宣传媒体,那些头号机会主义者。他们善于发现可供炒作的题材,'垮掉分子'运动就是题材,并且是可供大肆炒作的题材……'垮掉分子'的文学运动来得正是时候,说出了全世界各民族的千百万人盼望听到的东西。你不可能向别人灌输他不了解的东西。当凯鲁亚克指出路时,异化、不安、不满早已等在那里了。”
周报:你认为国内出版界是否有与“垮掉的一代”文学精神内涵相呼应的作品出现?
赵武平:回顾改革开放以来的文学发展,人们熟悉的王朔和刘索拉等人的小说,在某种程度上有些同“垮掉的一带”精神有契合的地方,但严格来讲并不能这么简单地对比。近来又有美国《时代》周刊等西方媒体,把卫慧、棉棉、春树和韩寒等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出生的一批作家,比作新一代中国的“垮掉一代”,也曾经在国内文学界和青少年研究界引起争议。尤其“80后”是飞速向前、急迫成长的一代。成长在中国发展最为迅速的时期,成长在一个价值观念急遽发展变化的时代,他们接受新事物的速度之快,生存方式及行为方式的多样及独立,都是上一代的人难以企及的。他们都热切地追逐时尚和前卫。
一位青少年研究专家指出,任何年代的人都有自己的特点,一概否定或者肯定都是不理智的。而且,对一个尚处于发展中的人群横加指责是不公平的,也是没有必要的。透过“春树们”叛逆的外表和行为,那些指责和批评者真的了解“春树们”的想法吗?外表和行动上的标新立异、混乱乃至堕落,一定就意味着思想的颓废或者道德的堕落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