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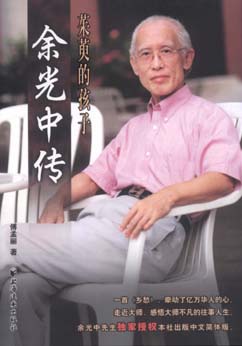 《茱萸的孩子——余光中传》记述了诗人余光中作为著名学者、诗人、散文家、翻译家、评论家70余年的生活与创作、亲情与友情、婚姻与爱情。 《茱萸的孩子——余光中传》记述了诗人余光中作为著名学者、诗人、散文家、翻译家、评论家70余年的生活与创作、亲情与友情、婚姻与爱情。
“我的小诗《乡愁》在大陆流传颇广,能背的人很多。这首诗像是我的名片,一方面介绍了我,另一方面却也遮住了我,使不少读者只见名片而不见其人,很方便地把我简化为‘乡愁诗人’定了位,《乡愁》只是我的门牌,这本《茱萸的孩子》才是我的大门,进得门来,才看得见我的庭院,进得了我的房屋。”——余光中
小袋鼠妈妈
1956年,余光中终于和表妹范我存结婚。这时他们来往已近6年了,彼此早已认定对方是自己惟一的选择,于是决定在9月结婚。快乐的准新娘开始筹划他们的婚事,这对心灵相契的人,一致反对铺张庸俗的婚礼和吵闹的喜宴,并且向往电影中看到的西方婚礼,安静,圣洁,简单,隆重。虽然他们都不是正式的教徒,不过范我存倒是经常陪着同学去做礼拜,参加唱诗班。她向卫理公会的牧师提出请求,牧师答应为他们主持婚礼。
9月2日,一对新人在卫理公会完成了婚礼,并在中山堂摆了15桌喜宴,宾客中包括了梁实秋、夏济安和蓝星诗社的诗友及余光中的同学。
结婚为女人一生的分界线,对于范我存来说,应该更是清晰。婚前的娇柔羞赧,在婚后不久就磨练成自信坚强。她住进厦门街一一三巷八号那栋占地一百多坪的日式房子,协助婆婆一同持家。身体素弱的她,在生下长女珊珊后,竟然渐渐强壮起来。从1958年到1965年,七年之间,她生下了五胎(其中惟一的男婴出生后三天不幸早夭),正如余光中早年形容的:
小袋鼠的妈妈,然后是两个三个,以至于一窝雌白鼠的妈妈……她已经向雷诺阿画中的女人看齐了。(《四月,在古战场》)
范我存回忆当年,经常是门铃、电话铃齐响,她一手挟着孩子,一边先抢接电话,要对方等一下,再奔下玄关去开大门;要不就是在厨房,把孩子放在推车里,忙着做饭。婚后两年婆婆去世,她开始主掌家务,最重大的一件事就是伺候一家人吃饭。余家全盛时期,大小共有八口,食指浩繁,食量惊人,还得兼顾营养可口。这对范我存是一大考验,但渐渐她也从中学到了讲求实际,而婚前的浪漫幻想也得暂放一边。
不过丈夫的文学活动,她始终坚持参与。蓝星诗社的成员把余宅当作总部,众诗人经常进出。后来余光中在师大教书,交游更广,家里又经常有学生来往,再加上公公余超英好客成癖,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厦门街余宅,简直人文荟萃。
为他腾出片写作空间
余光中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几乎都是女性。婚前他有母亲,婚后有妻子,然后是四个女儿,八条小辫飞舞。母亲去世后,岳母又搬来和他们同住。他身边的女人都爱他,宠他,敬他,让他,一切以他为中心。
外表娇柔的范我存,也许是深受母亲的影响,其实内心是极有主张的。她兼具传统与现代女性的优点和特质,虽然自己也很有才干,但是婚后完全奉献自我,不但是贤内助,更是贤外助。从内务大臣到外交部长,全由范我存一手担纲。
“她帮我摒挡出一片天地,让我在后方从容写作,我真的很感谢她。”余光中不止一次这样说。
“他忙起来,可以几天关在书房中,对你不理不睬,好像天塌下来都要由我自己去挡。当然刚开始我也不能适应,后来觉得他的创作的确很重要,我们都以他为荣,为他牺牲也就值得了。”范我存就这样从新婚的娇妻,一下子变成了四个女儿和一个丈夫的保姆,最后又成为他们的支柱。
婚姻之道
诗人余光中也是圣人余光中?
余光中的朋友们都一致推崇他的人格和德行。有一次林海音跟范我存数落男人的不是,最后的结论是:“没有像光中这么好的丈夫了。”余光中反问:“你怎么知道我好不好?”“我就是知道。”林海音信心满满地说。
丈夫好不好,当然只有范我存最清楚。“结婚后,他百分之百相信我、依赖我,虽然他不是常会说甜言蜜语体贴的丈夫,但是他以行动来表示对我和孩子的爱。”
“她的优点很多,”余光中说,“最重要的是,在精神上我们能契合,而且她能充分和我的事业、我的朋友融成一片。我们不但有共同的兴趣、嗜好,又有共同的朋友,婚姻怎么会不稳固呢?”
做夫妻40年了,两人鲜有吵架。余光中脾气虽急,但从不迁怒,而且脾气发过就放下了,心胸非常开阔。“家是讲情的地方,不是讲理的地方,夫妻相处是靠妥协。婚姻是一种妥协的艺术,是一对一的民主,一加一的自由。”这是余光中的“婚姻之道”。
余光中的情诗又多又动人,其中写给妻子的历历可数。范我存淡褐色的双眸和象牙白的肌肤,早年在《咪咪的眼睛》、《灵魂的触须》、《当寂寞来袭时》等诗中,都一再浮现,那是年轻时期的炽热恋情;晚年的《珍珠项链》、《三生石》、《东京新宿驿》、《停电夜》、《私语》、《削苹果》、《风筝怨》等,已转化成相依相偎的不渝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