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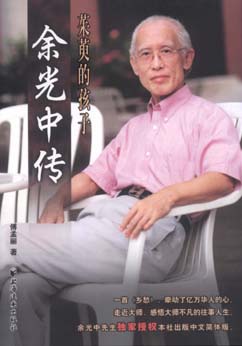 茱萸,很多现代人感觉很陌生,大概只有在王维的名句:“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中残存着记忆。相传茱萸有驱邪避灾的妙用,九月九日那天佩茱萸,登高饮菊花酒便可免祸。这个传说,沿袭了两千年。余光中生于重九之日,称自己为茱萸的孩子,正是出于对“母难”的纪念,更是对当时民族命运的一种祈望。 茱萸,很多现代人感觉很陌生,大概只有在王维的名句:“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中残存着记忆。相传茱萸有驱邪避灾的妙用,九月九日那天佩茱萸,登高饮菊花酒便可免祸。这个传说,沿袭了两千年。余光中生于重九之日,称自己为茱萸的孩子,正是出于对“母难”的纪念,更是对当时民族命运的一种祈望。
我惟一一次“直面”余光中先生,是在两年前,他在复旦作讲演。记得那时我与一群同学席地坐在大讲台下,仰视着余光中先生,他讲“中文与英文”,所讲内容已经模糊,惟有其儒雅的风范、睿智清冽的目光令我至今难忘。“余光中的书桌常保整洁,写稿、看书、批改作业,总见他正襟危坐,一笔一画,清清楚楚,就连大纲、附注之类,也都一视同仁,决不草率”,从他给这本传记写的新序手迹中即可“观风望气”。这种严谨、沉静的性格决定了他“三分之一是学者,三分之二是作家”。余先生看起来严肃、谨慎,但内心却是那样的丰富、充满热情。而傅孟丽女士的这本传记自然成为我“发现新材料”的绝好来源。了解余先生大概都是由于一首《乡愁》,他在序中说“这首诗像是我的名片,一方面介绍了我,另一方面也遮住了我……《乡愁》只是我的门牌,这本《茱萸的孩子》才是我的大门,进得门来才看得见我的庭院,进得了我的房屋。”进了房屋厅堂才发现余光中诗人的性情、文人的可爱,都不是“儒雅”二字所能统括的。
余光中一生酷爱音乐,尤其喜好西方古典音乐,他首次赴美就带回了上百张原版唱片。古典音乐的华丽、优雅、浪漫与深沉是余光中深深喜爱的,它们也滋养着他的诗风、文风。然而我们很难想象,这位严肃、沉静甚至看起来柔弱的诗人,后两次去美国,竟喜欢上了民歌和摇滚。他仔细聆听披头士的唱片,“发现他们的确多才多艺,从古典到蓝调,从爱丽丝仙境到荒原,披头士的艺术渊源广阔,变化丰富,表演生动,舞之蹈之,把摇滚乐演成一种立体而多元的诗。”文学与音乐在此际会,艺术的通感使余光中认识到:“如果诗人一味孤芳自赏,不能把握时代,争取读者及听众,就不能为现代诗开辟疆土。”此后其诗开始转向西方学习,节奏感强,洋溢着民歌风味。
在美国,余光中爱上开车,开着他心爱的白色道奇,驾着那匹“雪豹”,纵横在美国中西部的大平原上,享受高速的快意,一路绝尘的孤绝美感。从他的传记中可以发现,余光中从大学时代就爱骑脚踏车,以至于一度大量投稿为了赚足买车的钱。摇滚的恣放、驱车的不羁,正是诗人内心火热豪放灵魂的最佳表达,正是他诗歌柔曼儒雅步调下束裹着浪漫激情的来源。假如我们的诗人内心如外表一般的谨慎严肃,那么他就是“三分之二的学者”了。
他嗜书成癖,自称是资深的书呆子,称这种人“爱坐在书桌前,并不一定要读哪一本书,或研究哪一个问题,只是喜欢这本摸摸,那本翻翻,相相封面,看看插图和目录,并且嗅嗅(尤其是新的书)怪好闻的纸香和油墨味。就这样,一个昂贵的下午用完了。”这种癖病大概是所有旧式读书人的通病。这种“无目的把玩”的呆气,或许是文人的可爱之处,也许余光中往往在这种状态中得到了不少诗兴的灵感。
文人墨客自古好交游天下,余光中自不例外。虽然他曾抱怨其父早年如孟尝君般招待乡亲朋友,把家开放成旅馆餐厅,他不高兴时拒客不见,但是“后来他组诗社,家里也经常高朋满座;教书后,又常请学生回家吃饭,偶尔也会留客住宿”还是无意间秉承乃父好客的遗风。在“蓝星诗社”时期,以文会友,无数诗友过往切磋;他在任教香港中文大学时期“谈笑皆鸿儒,像宋淇、高克毅、思果……等等都是同事,又住得靠近,真是愉快极了。”友人造访,总能“宾至如归”。后来他自己也觉得“香港的那段岁月,是我一生过的最安稳、最舒服、最愉快的日子。”
《茱萸的孩子》以事为纲,以情为目,让读者全面认识了一个人,一个诗人,一位学者,一位长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