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凡人群第一期之进化,必依河流而起。中国有黄河、扬子江两大河流,其位置、性质各殊,故各自有其本来之文明,为独立发达之观,虽屡相调和混合,而其差别自不可掩。凡百皆然,而学术思想其一端也,以此形成南北思想之差异。王桐龄所著《中国历代党争史》即以此发端,历述先秦至清代学术思想及政治党派之分隔对立与生灭消长。下文节选自该书,颇有奇思迸发及妙趣横生之处,邀读者共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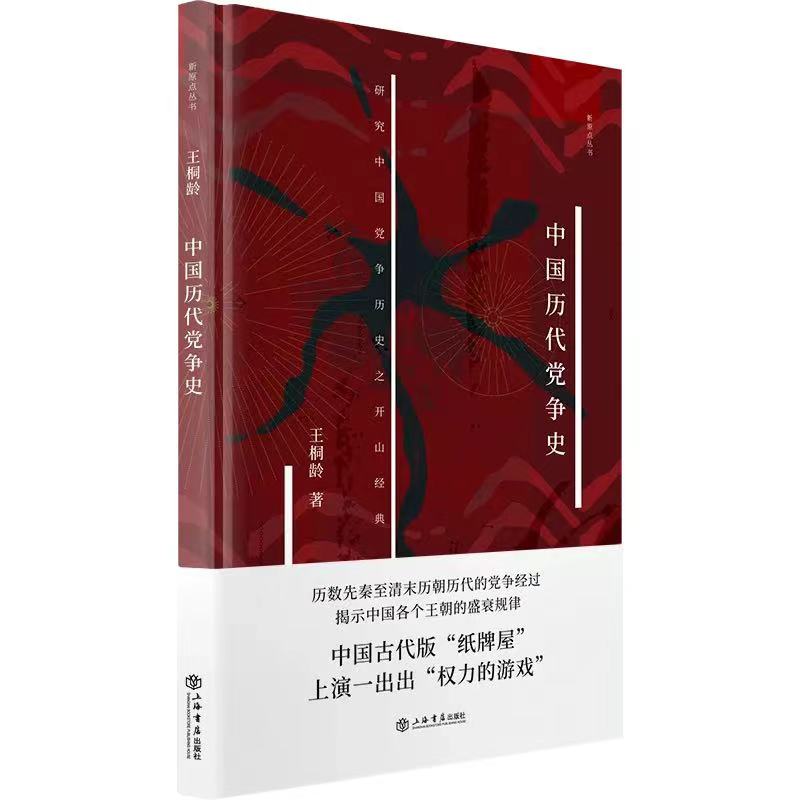
《中国历代党争史》
王桐龄 著
上海书店出版社
北地苦寒硗瘠,谋生不易,其民族销磨精神日力,以奔走衣食,维持社会,犹恐不给,无余裕以驰骛于玄妙之哲理,故其学术思想,常务实际,切人事,贵力行,重经验,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学说最发达。重家族,以族长为政治之本;敬老年,尊先祖,因而崇古之念重,保守之情深,排外之力强;则古昔,称先王,内其国,外夷狄,重礼文,系亲爱,守法律,畏天命。此北学之精神也。南方气候和暖,物产丰饶,谋生容易,其民族不必惟一身一家之饱暖是忧,故常达观于世界以外,始而轻世,既而玩世,终而厌世,不屑屑于实际,故不重礼法,不拘拘于经验;故不崇先王。又其发达较迟,中原之人常鄙夷之,谓为蛮野,故其对于北方学派,有吐弃之意,有破坏之心。探玄理,出世界,齐物我,平阶级,轻私爱,厌繁文,明自然,顺本性。此南学之精神也。
《中庸》曰:“宽柔以教,不报无道,南方之强也……衽金革,死而不厌,北方之强也。”《孟子》曰:“陈良,楚产也,悦周公、仲尼之道,北学于中国。北方之学者,未能或之先也。”是言南北之异点彰明较著者也。北派之魁,厥惟孔子;南派之魁,厥惟老子。孔学之见排于南,犹老学之见排于北也。孔子在鲁卫齐之间,所至皆受崇拜。乃至宋,则桓魋谋杀之。至陈蔡,则国人发兵围之。宋陈蔡皆邻于南也。至楚,则接舆歌以讽之,丈人揄揶之,长沮、桀溺目笑之,无所往而不阻焉。皆由学派之性质不同故也。北方多忧世勤劳之士,孔席不暇暖,墨突不得黔,栖栖者终其身焉;南方则多弃世高蹈之徒,接舆、沮溺、丈人,皆汲老庄之流者也,此民族之异性使然也。
孔老争雄南北,而起于其间者有墨子焉。墨亦北派也,顾北而稍近于南。墨子生于宋,宋,南北要冲也,故其学于南北各有所采,而自成一家言。其务实际,贵力行,实原本于北派之真精神,而其刻苦也过之。但多言天鬼,颇及他界,始创名学,渐阐哲理,力主兼爱,首倡平等,盖亦被南学之影响焉。
杨朱,老学之嫡传也。杨氏之为我主义、纵乐主义,实皆起于厌世观。《列子·杨朱篇》引其学说曰:“世事苦乐,古犹今也;变易治乱,古犹今也。既闻之矣,既更之矣,百年犹厌其多,而况久生之苦也乎?”又曰:“生则尧舜,死则腐骨;生则桀纣,死则腐骨。腐骨一矣,孰知其异?”盖其厌世之极,任自然之极,乃觉除为我主义、纵乐主义以外,更无所事事。故北学之有墨,南学之有杨,皆走于两极端,而处于正反对之地位者也。
以上所举,为后世门户之见、方舆之见所由来。所谓东西洋学派之倾轧,南北省界之区别者,即此种思想之变相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