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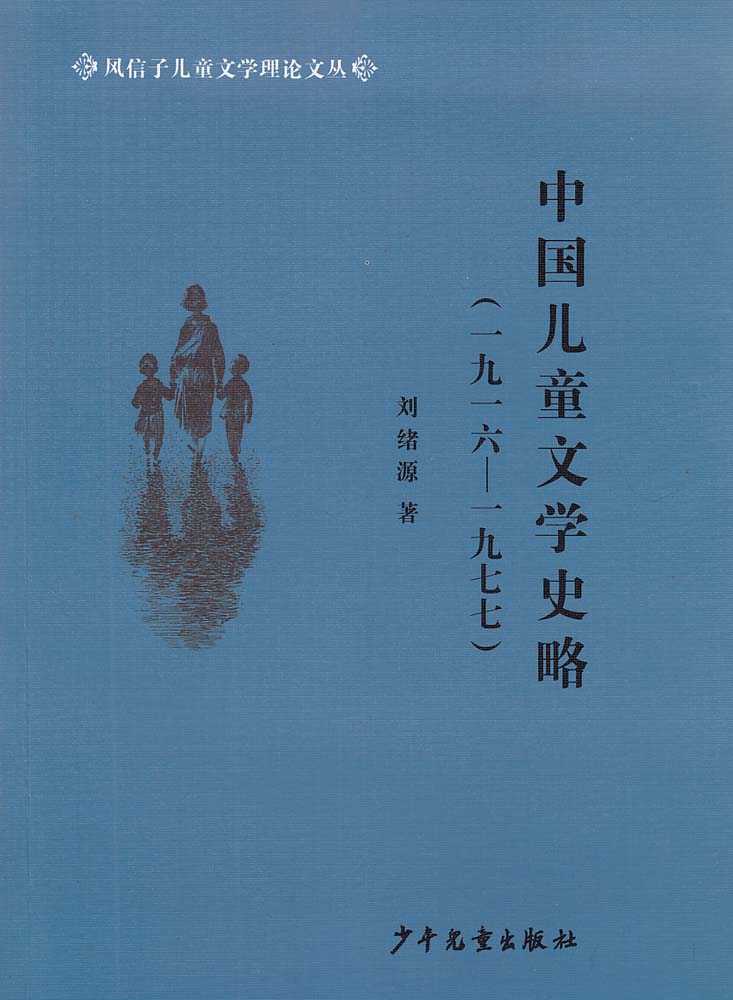 绪源老弟: 绪源老弟:
送了书给我(指《中国儿童文学史略:1916-1977》,刘绪源著,已由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极高兴。称我为“师”,近乎夸张,不能接受。谢蔚明先生编《文汇增刊》时,你可能编过拙文。
此书没有任何八股腔,难得。大的儿童也能读。
拜读之后,有两点感想——
“人之初,性本善”,未必。但“人之初,性本真”是可以成立的。儿童文学之难,之贵,在此。我三十年前,细读了《野妹子》,不错。
李卓吾的“童心说”甚佳。改革开放之初,儿艺演出《童心》一剧,人心一振。
如按弗洛伊德学说,儿童的表现,应该基本上属于“原我”、“本我”,而非“超我”。
斯坦尼认为演员演出角色,由第一自我进入第二自我。而现实生活中,不少人实际上也不是本来面目。因利害关系,说的是假话也。斯坦尼也太天真了。
“时代精神”与“纯文艺”,人们在理论上事实上蹈入误区的不少。《吕氏春秋》悬之国门,无人能“增损一字”,那是害怕吕不韦,不能认为《吕氏春秋》代表了时代精神。另一方面,“时代精神”似乎是急诊科的药物,而“纯文艺”则是不能立见功效的中药了。说的全是外行话,乞谅。祝
春安
蒋星煜
2013年4月19日
星煜先生:
谢谢您的信!今一早去单位,站在办公桌前,从一堆书报杂志中找出大札,当场拆阅。
一气读竟,满腹感怀。您的文字,愈益简略有味了,思路跳脱,断想联翩,每句皆有深意,都是自己思考过的内容,决不随波逐流。这让我想到晚年金克木先生的文字。金先生口若悬河,妙趣横生,思维跳荡,汪洋恣肆,跟他交谈真是难得的乐趣。您的性格谈吐跟金先生很不一样,但您到了94岁高龄,下笔为文,竟与金先生有几分神似,这是很奇妙的现象。
您说不能接受称“师”,害得我这封信里不敢再称。但我在这本新书上题写您的名字时,那个“师”字自然而然就跳出来了。这不仅因为书中有个关键的理论内容是在您的启发下,在和您讨论中,得以深化,并终于贯穿全书的;更因为在我写作的这几年,几次接到您的电话,对我鼓励有加,并有切实的指导。在我结束了报纸副刊的繁重编务,开始真正的著述生涯时,您来电话说,要抓紧这样的机会,这是一生难得的好时光,也是真有可能出成绩的时光,要珍惜。在我和李泽厚先生的对话《该中国哲学登场了?》和《中国哲学如何登场?》出版时,您又来电,对此作出高度评价,您还把这两次对话与我过去的周作人研究进行比较,说研究周作人也是重要的工作,但李泽厚与我们当下更切近,所以更具现实意义,值得做下去。我的这本《中国儿童文学史略》的“序二”,曾以《关于纯文学的论纲》为题发表在《文艺报》上,您读后,大感兴趣,来电和我讨论,并提出了一个很有趣的问题:“你文中说,纯文学不仅要有真情实感,还要有时代精神;那为什么‘文革’ 前被称为有‘时代精神’的一些戏剧、小说,现在回过头来看,都不是纯文学,反而大多是说教的、概念化的呢?”就是这一问,使我对“时代精神”的探讨又有新的进展,并将它渗透于整本“史略”。当这本新书终于写成出版时,您说我能不称您为“师”吗?
您信中谈的两个观点,也都有深度。一是说童心很难说是“善”,却可说是“真”。这是极高明的见地,也是您一生观察儿童,也观察社会人生的重要结论。儿童很难说有“善心”,他们最喜欢“恶作剧”,越是不让做的事越想做,看到谁摔跤了倒霉了还会拍手大笑。但要说“人之初,性本恶”,也不对,他们没有坏心,他们的“恶”其实都是游戏,他们没有暴力体验,更没有损人的目的。这就一个“玩”的年龄,他们的恶作剧也是玩,儿童文学要尊重这个“玩”的特性,也要在他们的“真”上发现童趣,这才能创作出最好最有趣的文学。正如您所说,“人之初,性本真”,他们不会掩饰,也不知克制,所以,这还是一个学习的年龄。怎样才可在学会克制并懂得关照他人的同时,仍能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童心之真呢?现在的社会是多么缺少这样的真啊!这正是儿童文学的任务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