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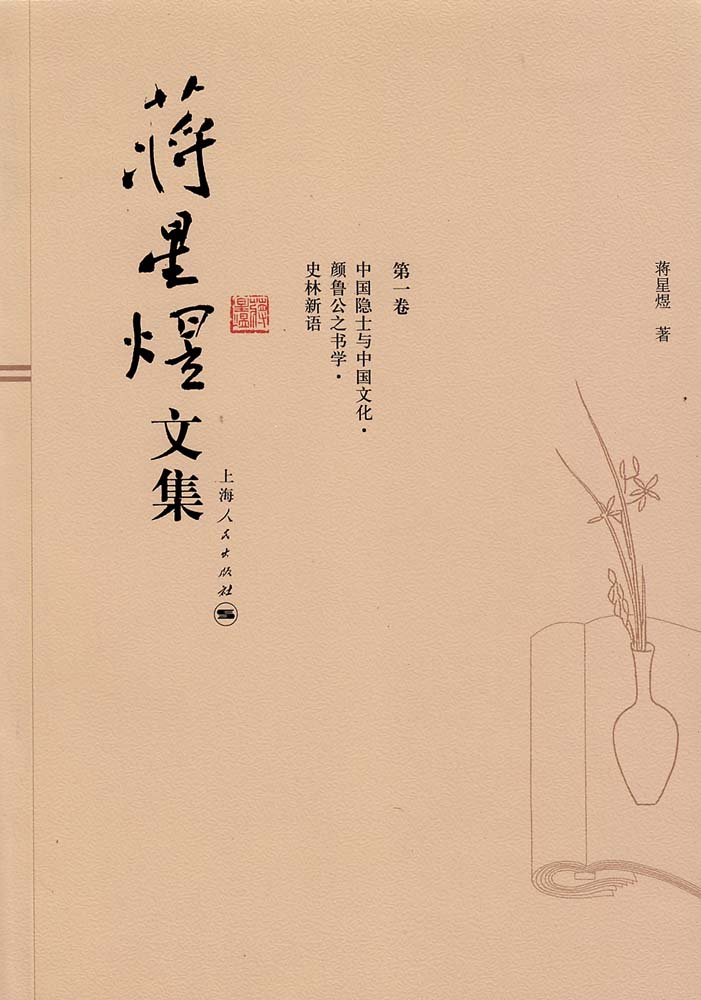 九十四岁的蒋星煜先生自青年时起即笔耕不辍,除“文革”时他因受迫害而被逼搁笔十年外,其写作期已长达六十年以上,著述总字数当不下三千万字,如今,先生将其著述中精华约千万字编成八卷本文集付梓出版,这是上海学界的一大收获,是应该予以热烈祝贺的。 九十四岁的蒋星煜先生自青年时起即笔耕不辍,除“文革”时他因受迫害而被逼搁笔十年外,其写作期已长达六十年以上,著述总字数当不下三千万字,如今,先生将其著述中精华约千万字编成八卷本文集付梓出版,这是上海学界的一大收获,是应该予以热烈祝贺的。
《蒋星煜文集》学术领域涉猎较广,其内容涵盖戏剧、文学(创作、评论)、历史、社会、书学、文献学等诸方面,第一卷收录了《中国隐士与中国文化》、《颜鲁公之书学》、《史林新语》三部专著,第二卷为 《况钟》(史传)、《海瑞》(史传)、《〈桃花扇〉 的研究与欣赏》,第三卷、第四卷分别为专著《〈西厢记〉的文献学研究》和《〈西厢记〉的研究与欣赏》,第五卷为专著《中国戏曲史钩沉》,第六卷是先生的文学评论及创作(散文、现代小说、自传)专集,第七卷为历史小说集,第八卷“文坛艺林备忘录”记叙文艺界的人和事。其实蒋先生尚有许多著述,尤其是发表于报刊间短文及一些序跋、评论,这次未收入文集,故翻阅文集后,不免有遗珠之憾。
说到学者的文集,近年此类作品的出版也已走向“市场化”,只要是会写作的人,并且又能筹到钱,出版文集应该不是难事,有的出版社也不大计较作者在某个学术领域有无地位、影响,反正只要有钱赚就给出,于是这“文集们”的质量,也就参差不齐了。就其学术水平而言,大致不外乎“真学术”和“浅学术”两个档次,“真学术”类文集是指严谨的、科学的、有真知灼见的著作,“浅学术”类文集包括的范围很广,即文集中看不到大部头著述,或在某一领域有一定影响的专著,而是大都散见于报纸杂志的短文或工作性报告文章,偶有论述之作,亦无病呻吟或人云亦云,四平八稳而难见独立见解,最终,这些东西终究会被时代和后人所淘汰。所以,我不主张编全集,而是应择其最优者编辑文集。以此标准而言,《蒋星煜文集》 当是一部聪明的、优中选优的文集,他毕竟是从全部三千万字的著述中遴选编著而成的,而他的学术成就又是举世公认的,这就保证了其文集是颇具含金量的真学术。
我之所以认定《蒋星煜文集》是近年上海出版的一部高质量、高品位、具有权威性的学者文集,是由蒋先生长期在学术上的耕耘劳作所决定的,先生此生研究成就颇多,但最足以显耀的突出在四个方面:一是关于中国戏曲史方面的研究,在 《中国戏曲史钩沉》卷中可以见到其具体的成果,对中国戏曲的发展脉络,对唐宋戏曲、元杂剧、明代昆曲、清代及近代戏曲的发展问题,多有所论述,特别是他对曾为中国戏曲发展作出过贡献的北方少数民族政权辽代的戏剧史,有精辟而独到的论述。
二是关于古典戏曲名著 《西厢记》和《桃花扇》的权威研究。就艺术成就及对后世戏剧、社会的影响而言,王实甫的《西厢记》是元杂剧中的头魁,当然引来从李渔、金圣叹、王国维到现当代的一代又一代的研究者。在当代的《西厢记》研究中,又数王季思、蒋星煜、戴不凡三位成就最高、影响最大,蒋星煜的研究,除从思想、艺术上入手之外,还着重在版本、文献学上下工夫,弄清了《西厢记》流传过程中的诸多沿革、枝蔓问题,可以说是独树一帜,应当能代表当代学术界的重要贡献。
三是他对况钟、海瑞的专题史研究,对史学界有特殊贡献。说到海瑞研究,蒋星煜当百味杂陈,他与这个明代的清官真是“缘分不浅”,早在1957年,他就出版了七万七千字的专著《海瑞》,比吴晗涉猎还早,而为《海瑞罢官》而身殉的北京史学家吴晗,直到1959年才写了一部一万五千字的小册子《海瑞》。不料是年政坛忽刮“海瑞风”,蒋星煜应报刊编辑之约在1957年4月17日 《解放日报》上撰写了《南包公海瑞》一文;此后,吴晗的京剧《海瑞罢官》也问世。不料到1965年,随着“阶级斗争”风声日紧,吴晗的《海瑞罢官》受到批判,并成为十年浩劫的“‘文革’先声”;在上海的蒋星煜自然也难逃厄运,不仅被诬为与吴晗“遥相呼应”(其实他们并无交往)而备受摧残,夫人也含恨离世。“文革”后拨乱反正,蒋星煜有关海瑞的研究成果重新获得肯定。2007年,内容经过增补的《海瑞》一书第四次出版。这段辛酸的学术往事,作者在文集中所收的《海瑞》一书“自序”、“后记”中已有叙述,我更想指出的是,蒋星煜对海瑞的研究,其学术中透出的沉重感,已超出了历史的范畴而成为另一种“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