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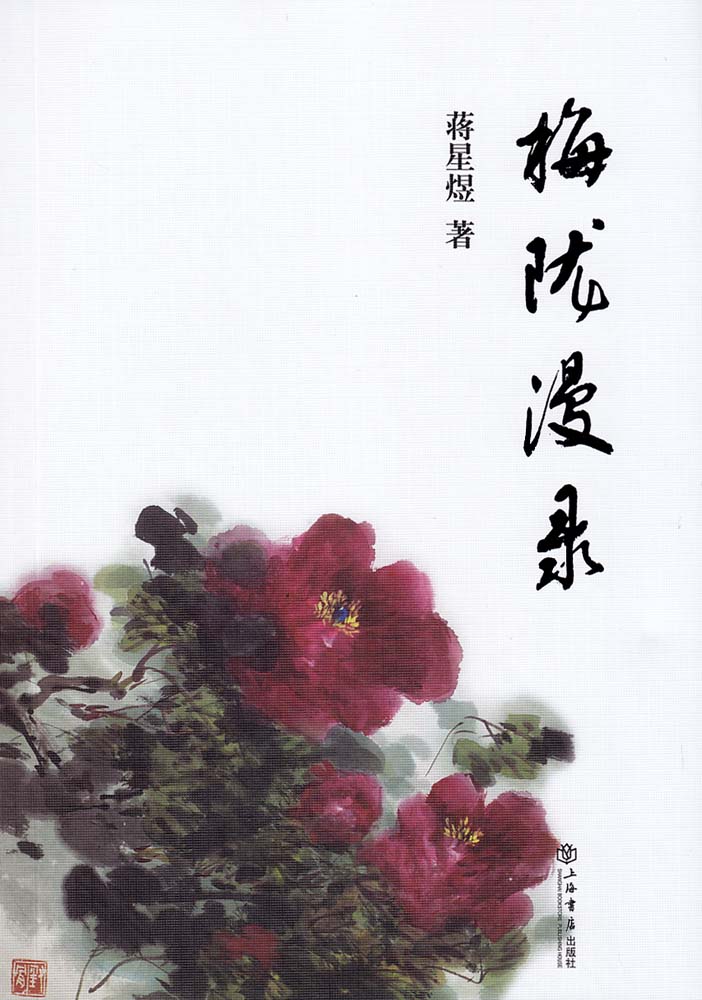 9月11日,来自全国各地的八十多位专家、学者汇聚上海文艺会堂参加“亦文亦史七十年,西厢桃花别样红——蒋星煜学术纪念活动”。主办方选择这个日子,大概是因为这一天是蒋星煜先生的生日吧?我有幸与会,忝陪末座,忽然想到:在蒋先生生前,我曾经用他的新书作为献给他的生日礼物,却并没有正正式式地为他贺过寿。今天我们这帮晚辈聚集在一起,给他老人家搞生日大派对,他在天上肯定笑眯眯地看着我们呢! 9月11日,来自全国各地的八十多位专家、学者汇聚上海文艺会堂参加“亦文亦史七十年,西厢桃花别样红——蒋星煜学术纪念活动”。主办方选择这个日子,大概是因为这一天是蒋星煜先生的生日吧?我有幸与会,忝陪末座,忽然想到:在蒋先生生前,我曾经用他的新书作为献给他的生日礼物,却并没有正正式式地为他贺过寿。今天我们这帮晚辈聚集在一起,给他老人家搞生日大派对,他在天上肯定笑眯眯地看着我们呢!
蒋星煜先生享年九十六岁,这本厚厚的大书在2015年12月18日那一天合拢了。我是他的资深粉丝,少年时代读他的两本小册子《海瑞的故事》《包拯的故事》,稍长读他在《青年一代》《舞台与观众》等报刊上刊载的历史故事新编,大学时代读他的史学专著、文史随笔,而他的戏曲史方面的专业著作,则是我在给他做责编期间系统阅读的。
我是1989年7月底进入出版行业的,供职的第一家出版社是上海辞书出版社,这是一家和蒋先生缘分颇深的出版社。蒋先生很早就参加了《辞海》“戏曲曲艺”的条目编写,我进社那会儿,蒋先生正在主编《元曲鉴赏辞典》,所以常来我所在的文艺编辑室交稿、谈事。我这个帮着老编辑抄抄《元曲鉴赏辞典》词目单的“新兵蛋子”见习编辑,连给老先生端茶递水的资格尚不具备,只能远远地向蒋公遥致注目礼而已。
2006年,曹正文老师主编的《百位名家谈读书》出版,上海书展期间有一个签名售书活动,曹老师邀请蒋星煜、邓伟志、叶辛、江曾培等名家出席活动。蒋先生那时已经八十七岁,自然得由我这个责编鞍前马后地接送。2006年8月10日,是我和蒋先生第一次正式见面的日子。那天中午,我早早地来到蒋先生家,还开心地收到一份见面礼——一本新出的《文坛艺林备忘录》签名本。听老先生的家人说,老先生刚刚因为心脏不适去医院住了几天接受挂水治疗,一诺千金的他尽管体弱,仍固执地要参加签售活动,家人也不敢违拗他。在去书展的路上,老爷子告诉我正在编选有关 《桃花扇》的研究论文集,已经有十万字的样子了;同时打算修订自己的成名作《海瑞》。作为粉丝的我欣喜不已,自告奋勇愿意效劳。也许是过于激动导致我指路不明,出租车停到了展览中心南京西路的出入口,我和蒋先生的外孙扶着老人家顶着大太阳缓缓行走,老人家体力几乎不支,低声地问:还没到啊?我走不动了。好不容易到了现场,看到热情的读者,他又来了精神,给一些读者题写了“读好书,好读书”等句子,签了大概半个多小时才提前告退。在上海书展的历史上,蒋星煜先生也许是参加签售活动年龄最长的一位嘉宾。
隔天我打电话去问候,他毫不见怪,我也就此终于走近老人家,开始了我们之间差不多十年的合作,荣幸地成为他的最后一位“御用责任编辑”,也可以说是他一位不记录在花名册上的“编外研究生”。2008年初,老爷子的《海瑞》《〈桃花扇〉研究与欣赏》同时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此后我先后为他编辑了《中国隐士与中国文化》《〈西厢记〉研究与欣赏》《中国戏曲史钩沉》(上下册)《史林新语》《山水对人性的折射——蒋星煜旅游散文选》 等著作的单行本。而八卷本《蒋星煜文集》的出版,是我们近十年合作收获的最大最美的果实;尽管出版的过程,既艰苦又煎熬,但回想一下还是觉得很过瘾,在我的出版生涯中,这套大书无疑是最有纪念意义的。
老爷子编文集,选文章要求极严,一般常见作者做加法,而老爷子则是“反其道而行”——毫不手软地做减法。文史札记集《以戏代药》是他多年来为《新民晚报》《羊城晚报》等报刊所写短文的结集,1980年花城出版社初版,2007年上海远东出版社增订再版,很受读者的欢迎。文集最初的目录中收了此书,但后来他觉得这些文章太零散,除保存少量篇目,其余全部舍弃。文集也从原来拟定的九卷“瘦身”为八卷。
蒋先生生命的最后两年,因为视力严重下降,一天只能工作一个多小时,但他还是为报刊写了很多内容厚实的文章,我们经常能看到他在《新民晚报》“国学论谭”上发的整版文章,除了敬佩还能说什么呢? 有一次他要写关于白居易的牡丹诗的研究文章,打电话让我帮他找书,我赶紧从网上买了《白居易评传》、《白居易资料汇编》两种书给他送去。还有一次他写一篇有关《清明上河图》的文章,又让我帮忙找宋人笔记,我知他心急,立即去隔壁的古籍书店找了两种快递给他。他的工作效率之高常常让我惊叹。
编选文集是蒋先生晚年最重要的一项工程,当文集在他九十四岁出版时我深感欣慰,同时觉得我这个“御用责编”的工作大概可以画上句号了。没想到后来又收到蒋先生的信说要再编一本新的文史随笔集《梅陇漫录》,我很激动,立即表示一定还是自己做责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