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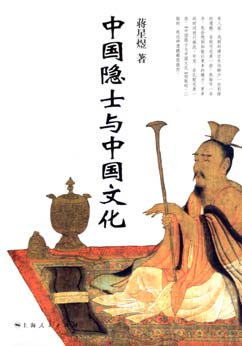 日前我收到90高龄的戏曲史家、文学家蒋星煜先生寄来的《中国隐士与中国文化》,阅后深感这是值得文化人一读之书。他写这部书时才20岁,受到学者梁漱溟先生的关注,并在《中国文化要义·绪论》中说:“蒋星煜先生著《中国隐士与中国文化》一书,指出‘隐士’这一名词和它所代表的一类人物,是中国社会的特产,而中国隐士的风格和意境,亦绝非欧美人所能了解。”过了70年后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再版,可见它的价值。记得有一年,我收到他一口气出版的4种书,近百万字,煌煌巨著,堪称奇迹。这是一种怎样的毅力,怎样的非凡。怪不得在上海举行的蒋星煜先生学术创作活动65周年座谈会上,有人戏称他为“妖怪”。妖者,凡人难以企及也。
日前我收到90高龄的戏曲史家、文学家蒋星煜先生寄来的《中国隐士与中国文化》,阅后深感这是值得文化人一读之书。他写这部书时才20岁,受到学者梁漱溟先生的关注,并在《中国文化要义·绪论》中说:“蒋星煜先生著《中国隐士与中国文化》一书,指出‘隐士’这一名词和它所代表的一类人物,是中国社会的特产,而中国隐士的风格和意境,亦绝非欧美人所能了解。”过了70年后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再版,可见它的价值。记得有一年,我收到他一口气出版的4种书,近百万字,煌煌巨著,堪称奇迹。这是一种怎样的毅力,怎样的非凡。怪不得在上海举行的蒋星煜先生学术创作活动65周年座谈会上,有人戏称他为“妖怪”。妖者,凡人难以企及也。
蒋老出名很早,抗战时期已从事新文学活动,显示出不凡的能量,尤其是文学评论,我曾找来读过,洋洋洒洒,说理透彻,文气极盛,自然流畅,令人信服。1944年在《大公报·文艺》副刊上发一版半长文《东北作家论》;1945年在由陈原主编《民主评论》刊发长文《论〈华威先生〉》,至今仍作为研究张天翼的重要资料;同年在《新文艺》上发的《论阿Q周围的人物》,竟然在2000年被人民教育出版社入选高三语文教科书,可见影响之深远了。蒋老还写出一批有品质的散文,如1941年撰写《威尼斯的忧郁》整版刊发在孙伏园主编的《中央日报》副刊上,还有《祖国怀念者》、《荒漠琐记》等。
我知道蒋星煜先生大名是“文革”之初,记得当时有篇署名丁学雷的《〈海瑞上疏〉为谁效劳》批判蒋星煜的文章。我以批判为名,向学校图书馆借来那本薄薄的《海瑞》读了起来,觉得蛮有味道,那年我才15岁,心里还暗暗佩服海瑞为民请命的精神。粉碎“四人帮”后,我看到蒋老不少戏剧评论文章,字里行间洋溢着澎湃的激情,以及他的睿智和活力。特别是《西厢记》研究尤为突出,怪不得他将自己的书斋取名为“西海书屋”。西者,古典名剧《西厢记》;海者,明代清官海瑞是也。
我第一次与他见面是9年前在《上海作家散文百篇》一书的签名活动时,当时有近70位作家前来光明中学签名。蒋老是前来签名的第三位年长者,徐中玉、钱谷融先生之后就数他了,他正患着感冒,还是由女婿陪同而来的,他热心于公益事业,是最早来到的作家。此书6册签名本,拍卖获得善款18.8万元,全部捐献给上海市慈善基金会。
后来在作协活动时,我们有机会经常见面,给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华师大为庆贺徐中玉九十华诞那次。蒋老衣冠楚楚,依旧来得较早,旁边座位空着,我向他请安并在他身边坐了下来,想不到他对我研究古陶瓷十分关注。他说:“我对古玩也喜欢,我的老邻居是古玩商,解放初我曾参与军管会文艺处查处文物工作。你写的鉴赏古陶瓷文章,开创考古新文风,通俗易懂,知识性、趣味性、可读性都很强,还有文采。你撰写《寻访中华名窑》是前无古人的事业,至今还没有人这样做过,功德无量。过去顾颉刚、夏鼐等考古前辈都用半文不白的语言写考古文章,顾颉刚等学者因是从旧学过来的,情有可原。现在考古学者写的文章,也摹仿,实在是个误区,有的甚至认为自己的文章别人读不懂,说明学问高深,其实不然。考古学者应从高楼深宅里走出来,面向大众,并为读者所理解所接受,这才是有意义的事情。但是你要注意写文章所用的史料必须准确无误,处理好与考古界同仁的关系,主动和他们交朋友并逐步得到他们的认同。”这些话可谓语重心长,对我教育帮助很大。
说到蒋老,海瑞总该谈一下的,有关海瑞的事不仅影响了蒋老人生,也影响了中国现代史的进程。蒋老说:“研究海瑞,一开始坐了三年冷板凳,写出了历史人物传记《海瑞》。1957年于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1959年,据说当时毛泽东主席提出,要大家学习明代清官海瑞的刚正不阿的精神,海瑞忽然成了大热门,于是又有关于海瑞的小说、戏曲研究、文集版本等各方面的约稿。《解放日报》请我写《南包公海瑞》和《李世民与魏徵》的文章。发表时倒并没有受到什么责难,可是‘文革’一开始,这两篇文章即被打成‘大毒草’。凡是提到海瑞都遭殃,我写这篇文章自然也埋下了祸根,从此陷入苦难的深渊,被批斗、隔离,家庭也遭株连。所幸的是当时的领导主动承担了责任,才使我勉强过关。直到‘文革’噩梦结束,在《解放日报》老总编辑魏克明同志再三叮嘱下,写了《魏徵精神何罪之有》。刊发时,魏克明同志在病榻上还专门为此文写了‘编者按’。”此后,蒋老又重新信心百倍地拿起笔来,一口气为《解放日报》写了《司马迁》、《刘邦、萧何与韩信》等历史小说。到了上世纪80年代后期蒋老还陆续在《解放日报》主办的《上海小说》上发表了《捉刀人曹操》、《柳公权书法谏君》等历史小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