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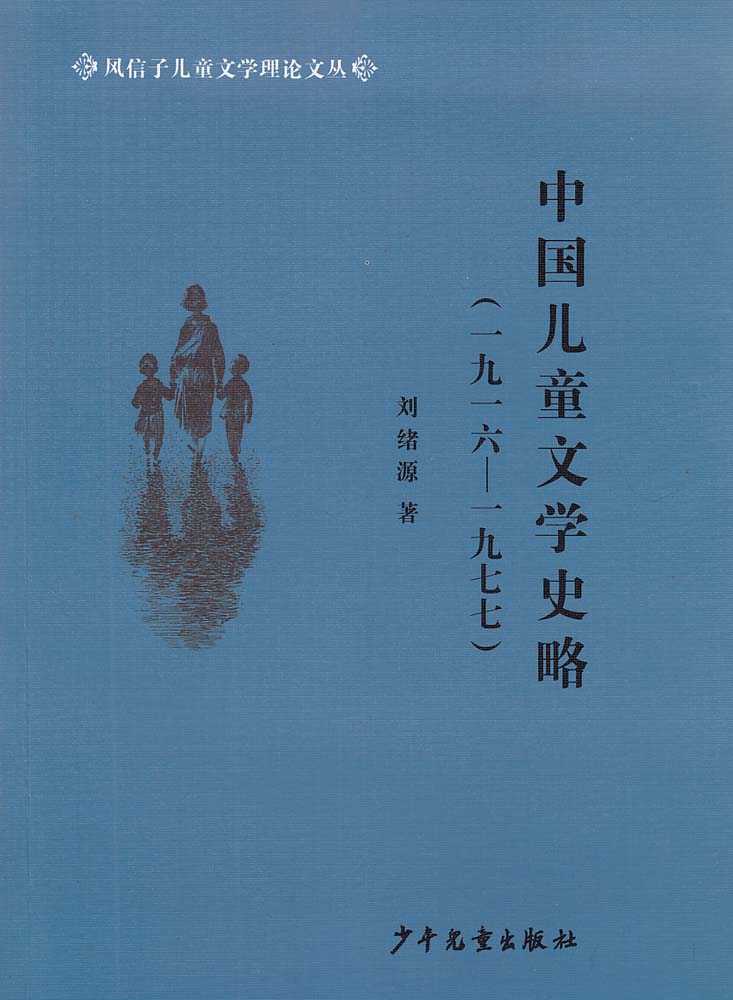 当我们回望行进中的新世纪儿童文学时,会发现那些能够点燃儿童文学创作与出版激情和灵感的艺术生长点:幻想文学、幽默文学、图画书、动物小说、网游文学……都已轮番登场并持续展示了有目共睹的市场实力。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2013年的儿童文学必然具有“守成”的色彩,当我们把这一年从一个连续性的时间轴上切下来单独观察时,我们不得不经常使用一个词:继续——它既可以在前些年创下的基业的“阴凉”中惯性前行,同时又要体味在已经开创的艺术之路上跋涉到纵深处的艰辛和繁难。2013年的儿童文学在繁华热闹中有一种静水深流的姿态。 当我们回望行进中的新世纪儿童文学时,会发现那些能够点燃儿童文学创作与出版激情和灵感的艺术生长点:幻想文学、幽默文学、图画书、动物小说、网游文学……都已轮番登场并持续展示了有目共睹的市场实力。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2013年的儿童文学必然具有“守成”的色彩,当我们把这一年从一个连续性的时间轴上切下来单独观察时,我们不得不经常使用一个词:继续——它既可以在前些年创下的基业的“阴凉”中惯性前行,同时又要体味在已经开创的艺术之路上跋涉到纵深处的艰辛和繁难。2013年的儿童文学在繁华热闹中有一种静水深流的姿态。
“童年回忆性书写”的热潮
在2013年的儿童文学创作中,作家们(无论是友情出演的知名成人文学作家,还是儿童文学作家本身)对回望自己的童年表现了极大的兴趣,形成了一股集体“童年回忆性书写”的热潮。如赵丽宏的《童年河》(福建少儿社)、常新港的《青草的骨头》(明天出版社)、陆梅的《格子的时光书》(接力出版社)以及明天出版社推出的“我们小时候”丛书,(包括王安忆的《放大的时间》、毕飞宇的《苏北少年“堂吉诃德”》、苏童的《自行车之歌》、迟子建的《会唱歌的火炉》、张梅溪的《林中小屋》和郁雨君的《当时实在年纪小》)等等,这些作品不是或者说不仅仅是对个体童年岁月的深情追怀,而是有明确的读者意识,即这些书是(或主要是)写给今天的孩子看的。这些主要出生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和70年代的作家们,通过“童年”和“成年”相互交织的双重视角,引领我们既抵达了童年现场,也抵达了对童年本身的深切省察。在他们的笔下,怀旧并不是主色调,他们的回望是面朝当下的。可以说,在这些作品中暗暗隐藏着这样的期望——童年往事在岁月的流逝中不但酝酿成了甜美忧伤的乡愁,而且沉淀下许多富有价值的体悟。他们愿意把这些体悟和今天的孩子对话、交流,甚至渴望有一些行将消逝的文化被记忆、被传承。又甚或,在他们对过去的眷恋的目光中有对当下童年精神生活缺失的指证和确认。
这些小说或散文中为“风景”留下了饱满的空间。评论家刘绪源评价《童年河》的风景描写时用了“铺张”一词。在《苏北少年“堂吉诃德”》里,更是用了一整章写“大地”:麦地、稻田、棉花地、自留地、荒地……在无垠的田野上,少年毕飞宇倾听着“泥土在开裂,庄稼在抽穗,流水在浇灌”。这种“铺张”的风景描写恰恰写出了那个物质奇缺时代的孩子们,他们有他们的财富,他们的奢侈——不管生活多么苦难,他们拥有一片自己宽阔的原野,一片不管是从地理学意义上还是从精神意义上都可以称之为“家园”的土地。毕飞宇说:“如果你的启蒙老师是大自然,你的一生都将幸运。”这一点映照出了今天的孩子尤其是都市孩子的不幸,他们远离大自然,远离动物植物,被拘束在狭窄的空间里。在迟子建的笔下,“炊烟是房屋升起的云朵”;在赵丽宏的笔下,“芦苇是河流绿色的花边。”当下的孩子,也许没有机会去亲身体味这样美丽而诗意的感受。当作家们写下了那个时代的童年刻骨铭心的饥饿感,也无言地指认了这个时代童年的另一种匮乏。
这样的反思不但指向童年的空间问题,也指向童年的时间问题。在陆梅的《格子的时光书》里,故事发生的时间背景是上世纪80年代初,那个时候的父母老师远没有今天的这么严格和功利,在小说中,几乎看不到格子的父母对她学业的催促,所以她可以拥有一整个暑假自由地“游荡”。她的脚步可以放任地抵达芦荻镇的每一个角落,尽管小镇的生活是那么平静、波澜不惊,它依然蕴藏着生命的全部喜悦与悲凉。这个暑假看似格子什么都没干,似乎就是“游荡”,但她的内心却从没有停止感受、思考和体味。也许在大人们的眼里,她还是个孩子,其实她的内心是那么敏感、丰富,来自生活中的风雨已经在她的心灵上敲打出或哀婉或欢乐或舒缓或快捷的一首首乐曲。也许她没有像今天的孩子这样被送到各种各样的补习班里去,但她却可以向整个生活学习。这部小说让人不得不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即我们需要不需要给童年以闲暇,我们是否相信孩子具有自我探求的能力和愿望?我们是否要占据他们所有的时间,把他们锁在课本上、作业中,而不留给他们一点自我探索的空间?
在岁月的风沙里能够提炼出金子般的箴言,不过,这些作品里没有训诫,作家们只是像朋友——即便像父亲,也是“多年父子成兄弟”这种类型的父亲,平等地与孩子们对话,用温暖的、平和的调子说出生命馈赠给他们的感悟。《青草的骨头》说的是“原谅”,经历过挫折、磨难、背叛之后,依然能够选择谅解,选择宽恕,选择追随爱、善良和同情,这是小说中一个13岁男孩对于成长的深切领悟。在《苏北少年“堂吉诃德”》里是“分享”。抚养自己多年的老奶奶,在分别的时候,一无所有的她选择把自己珍藏的来年要做种子的蚕豆作为礼物送给少年毕飞宇。这样的“分享”见证了真爱的力量。在《童年河》里流淌的,更是一种平凡朴实却让人终生难忘的亲情、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