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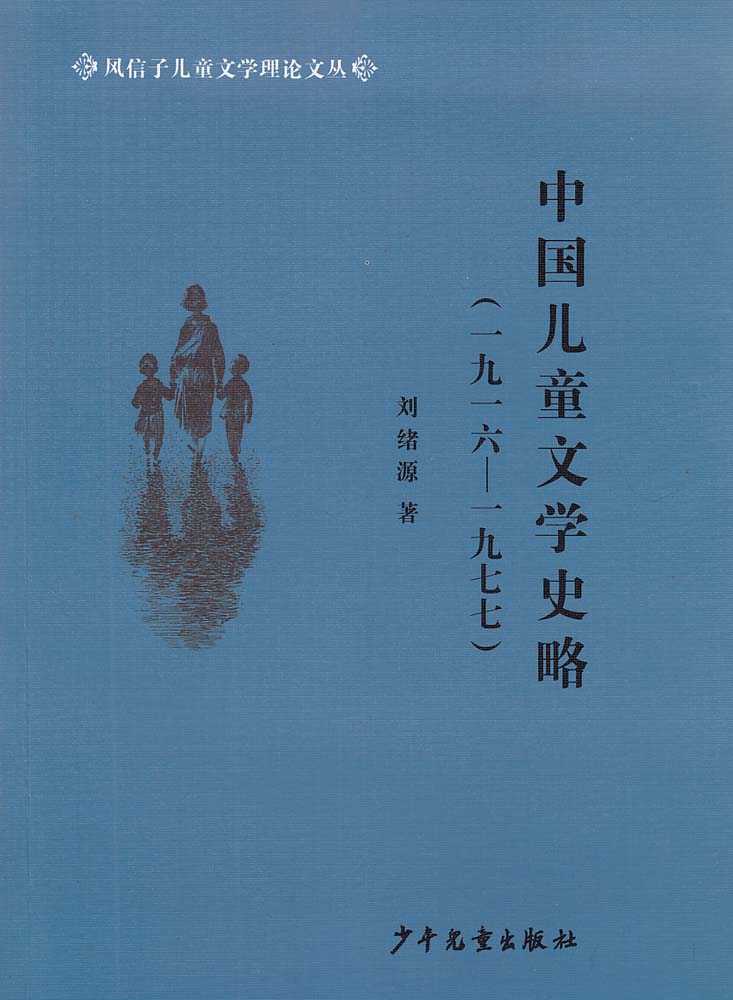 中国儿童文学史的研究与写作,不但与成人文学史写作相比是滞后的,而且相较于儿童文学的理论与批评也是薄弱的。既有的儿童文学史著作,在资料的收集整理上很见功夫,也显示出在儿童文学史观、视角选取和理论资源借鉴等方面的积极探索和尝试,其中最关键的似乎还在于“史识”与“史观”的问题。近期出版的《中国儿童文学史略(1916-1977)》(以下简称 《史略》),将这一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它不是史料长编,也没有对这段历史中的儿童文学现象、作家作品进行全面论述,作者自称为相对成系统的“书话”合集也不无道理。它遵循大体的时间线索,挑选了部分优秀作品进行鉴赏与批评,把对于纯文学理论的思考融入其中,探寻这些具有真情实感和时代精神的作品是以何种审美的方式给文学史创造了新的形式或者内容,以及它们彼此间横向与纵向的关系。本书最大的突破就是在文本细读中体现的许多深刻“史识”及其一以贯之的“纯文学”史观。 中国儿童文学史的研究与写作,不但与成人文学史写作相比是滞后的,而且相较于儿童文学的理论与批评也是薄弱的。既有的儿童文学史著作,在资料的收集整理上很见功夫,也显示出在儿童文学史观、视角选取和理论资源借鉴等方面的积极探索和尝试,其中最关键的似乎还在于“史识”与“史观”的问题。近期出版的《中国儿童文学史略(1916-1977)》(以下简称 《史略》),将这一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它不是史料长编,也没有对这段历史中的儿童文学现象、作家作品进行全面论述,作者自称为相对成系统的“书话”合集也不无道理。它遵循大体的时间线索,挑选了部分优秀作品进行鉴赏与批评,把对于纯文学理论的思考融入其中,探寻这些具有真情实感和时代精神的作品是以何种审美的方式给文学史创造了新的形式或者内容,以及它们彼此间横向与纵向的关系。本书最大的突破就是在文本细读中体现的许多深刻“史识”及其一以贯之的“纯文学”史观。
一、把儿童文学还给文学史:从史的角度发现儿童文学的秘密
儿童文学史的写作需要借助一种史的眼光,将某一时期的儿童文学放置到历史的脉络中进行考察,通过时间维度发现儿童文学中的新问题及其原因,在相互联系对比中寻找其规律并给予作品客观的评价和定位,“发现不写史、不从史的角度研究就无从看到的秘密”(刘绪源语)。《史略》就藉此发现了中国儿童文学很多有价值的“秘密”。
比如它打通了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政治童话”与建国后十七年“教育童话”的壁垒,发现了二者之间的血脉关系,以及“非主流”作品对其“图解”模式的突破。三十年代张天翼的《大林和小林》是公认的童话里程碑式的作品,《史略》 在充分肯定它的艺术成就的同时,也指出其极不成功的一面:它开启了图解“革命理论”的创作之路,并且因为有成功一面的遮掩,所以遗害更甚。四十年代后期产生了一大批“政治童话”,而且这种“图解”、主题先行的模式延续到了建国后,“十七年”儿童文学就被定义为“教育儿童的文学”,儿童文学成了医治孩子缺点错误的“糖衣药丸”,由此前“政治的工具”变为“教育的工具”,正是“政治童话”的自然延伸。但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史略》又挖掘出了一些形象大于思想、趣味大于教育、以文学审美突破教育童话框架的“非主流”作品的艺术价值,并大力阐述了这些作品的文学史意义。这也改变了此前我们对十七年儿童文学“一刀切”的片面认识,开始重新看待那些“戴着镣铐跳舞”也仍然跳得很好的堪称纯文学的作品。
同样,通过对建国前后大量战争题材儿童小说的历史考察,《史略》发现这些战争小说大都具有“孩子给敌人带路”这一雷同的情节模式,并从当时的历史环境与文学环境中深挖根源。在战争结束之后的“十七年”,这种现象反倒变本加厉很发人深思,那时的集体生活新范式延续了战争年代的军事化生活,儿童生活也很难“私人化”,此类小说中儿童唯一可以作为主角的战争行为就是“带路”。然而个别突破这种套路的作品如刘真的《长长的流水》、萧平的《玉姑山下的故事》等,则描写了战斗集体中儿童的“私人生活场景”,写出了具体个人的感情和真实的“战争中的孩子”,而非模式化的“孩子的战争”,从而具有永恒的艺术魅力。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史略》 还指出我们的战争文学存在对战争的“神圣化”渲染,而忽略了如何“走出战争”,实为洞见。从历史的角度看,排除“私人化”还导致了建国后校园小说两种范式的差异,其中主流的一种是写私生活被剥夺、完全生活于“组织”中的儿童,并最终将其“样板化”而变成了概念化的模式;另一种则是极少数的“私人生活场景”的写作,如杜风的《钓鱼去》和萧平的《海滨的孩子》,都具有永恒的纯文学性质,这些都是对于儿童文学史的真知灼见。
二、把儿童文学史还给文学:以纯文学眼光进行文本细读
《史略》中的所有观点和结论都是通过文本细读获得的,而其依据就是纯文学的审美性鉴赏和评析。也正因为这些细节丰满的解读,使得这部文学史虽为史“略”却并不显单薄。通过这样的细读,我们也发现了许多此前儿童文学史所忽略的东西,让我们领略到某些作品的精妙之处。比如通过对凌叔华短篇儿童小说《搬家》的解读,指出它在人物关系、照应和伏笔、精致的结构等方面,“接续了《红楼梦》和《儒林外史》的传统”,这种将故事隐在生活背后的写法,使儿童文学“静美、斯文、深邃、悠远”,作者同时表达了对新时期尤其九十年代以后儿童文学创作的批评与担忧:安安静静写日常生活的作品越来越少,故事的骨骼愈益外露,文学阅读的趣味日渐淡薄,儿童如果缺失静心阅读的机缘,细腻的艺术感觉能力又如何获得?此批评可谓入木三分,批评者的拳拳之心尤为感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