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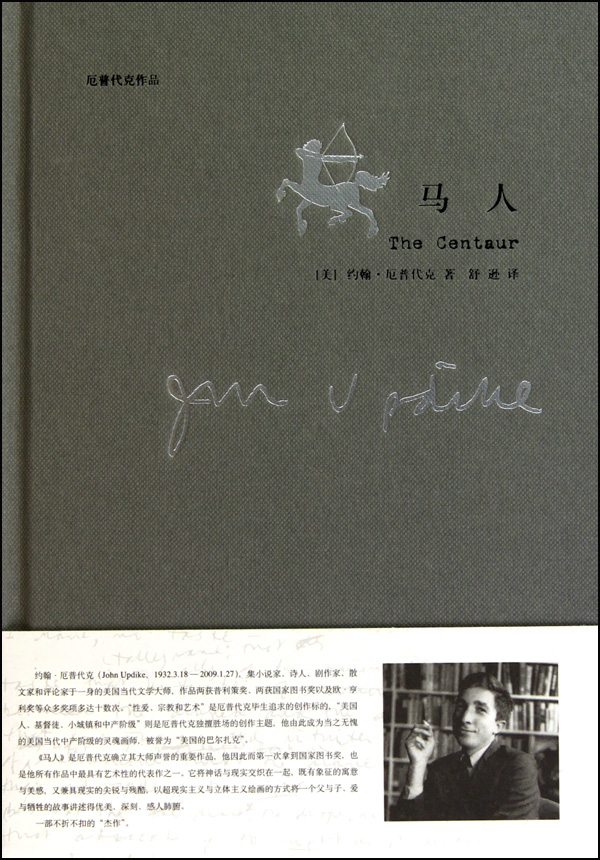 以“兔子四部曲”闻名于世的美国当代著名作家厄普代克,被誉为“美国的巴尔扎克”。如此高的评价,似乎只有读过他大部分作品的人,才能加以验证。不过,看了上海译文出版社不久前出版的厄普代克的代表作之一《马人》,笔者以为,上述美誉有夸张的成分,但也不能算过分。就反映生活的深度和质感而言,《马人》这部融现实与神话于一体,以现实的残酷、主人公命运的悲情反衬理想世界的美好与虚幻的杰作,为作家第一次摘得了美国国家图书奖,一举确立了厄普代克在美利坚乃至世界文坛的地位。 以“兔子四部曲”闻名于世的美国当代著名作家厄普代克,被誉为“美国的巴尔扎克”。如此高的评价,似乎只有读过他大部分作品的人,才能加以验证。不过,看了上海译文出版社不久前出版的厄普代克的代表作之一《马人》,笔者以为,上述美誉有夸张的成分,但也不能算过分。就反映生活的深度和质感而言,《马人》这部融现实与神话于一体,以现实的残酷、主人公命运的悲情反衬理想世界的美好与虚幻的杰作,为作家第一次摘得了美国国家图书奖,一举确立了厄普代克在美利坚乃至世界文坛的地位。
《马人》的情节并不复杂。乔治·卡德威尔是美国某小镇上的中学生物教师。他以教书的微薄收入,供养着岳父、妻子和正在上中学的儿子彼得,勉强维持一个三代之家的生活。人过中年的卡德威尔深感身心憔悴,对自己碌碌无为的生活既不甘,又无奈。一天,他偶然撞见一位女同事衣衫不整、神色慌乱地从校长吉摩尔曼办公室跑出来,因而闯了祸,面临着被奸诈的吉摩尔曼解雇的危险。卡德威尔万念俱灰,甚至想一死了之。痛苦和死亡的心理暗示使他怀疑自己患了癌症。然而,当X光检查告知他安然无恙后,他非但没有释然,反而更加难受。因为他无法以死获得解脱,惟有继续履行他的生之职责。
这部小说的名字来自希腊神话中一个半人半马的形象客戎。客戎上半身是人,下半身为马,他在一次混战中被一支毒箭射中,痛不欲生。由于是神,他无法死去,于是请求天神宙斯答应让自己去死,以换取被缚的普罗米修斯的解放。宙斯最终同意了。厄普代克借用客戎的神话故事,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小说一开始,卡德威尔上生物课时,被恶作剧的学生用钢钎制成的一枝箭射中脚踝,他疼痛难忍,不得不离开教室去治疗。这一情节显然是客戎故事的“克隆”,隐喻了他如同客戎被毒箭射中,其实就是他在现实生活中忍受的痛苦和折磨的写照。而在小说的第一章中,作家用亦真亦幻的写作手法,将卡德威尔与客戎的形象重叠合一;并且随着故事情节的深入,主人公内心世界与现实生活矛盾冲突的加剧,隐喻出卡德威尔在生活中承受的种种磨难,是为了他的家庭,为了儿子将来的前途所做出的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牺牲;就像客戎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换取了普罗米修斯的新生。因此卡德威尔像客戎那样有宗教般的悲剧性,只是凡夫俗子的他缺乏神界的客戎的崇高美。
给卡德威尔看病的阿波顿医生的一句话耐人寻味:“我们犯了两个错误:一个是站起身来直立行走,另一个是开始思考。”这两个“错误”是人之所以区别于动物的标志,直立行走意味着人从此要承受外界随时给予他的各种苦难和打击;思考假如没有答案,则会给心灵带来无尽的困惑和痛楚。卡德威尔就是在这双重的折磨中,憋屈地生活着。虽然他有过带领校游泳队参加运动会获得的自豪感(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不会游泳);有过和初恋情人海斯特重叙旧情并即兴朗诵诗歌的欢愉,以此象征往昔的美好,反衬现实的灰暗,可是,卡德威尔的整个人生就是一部不断与挫折苦斗的辛酸史。自从他青年时代满怀爱国热情参加一战,退役后他就开始面对现实的冷酷和人生的种种不如意,靠着一份体育奖学金,他半工半读完成大学学业;结婚不久就遭遇美国上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由于失业而走投无路,只得投奔岳父,好不容易在岳父生活的小镇上谋得了一份中学教师的工作。为了这份养家糊口的工作,卡德威尔含辛茹苦,忍辱负重,就像书中形容的那样:“如果人是马,卡德威尔是一匹做苦活的灰斑马,有些不足挂齿却也不一定出自劣种……”
小说结尾部分,客戎独自在大雪中走向抛锚的别克车。这里,神话和现实再次交融,神话折射现实。这辆老别克曾屡出故障,造成卡德威尔看完病后带彼得回家的路上被困顿了三天,它象征了卡德威尔失败的生活;但客戎走向这辆老别克,则隐喻了卡德威尔接受了自己的命运,使卡德威尔的自我牺牲最终染上了悲剧英雄的色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