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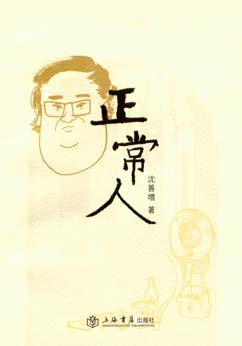 小说家功力的高下,显示在自己讲故事的方式中。所谓艺术造诣,或许就是有能耐将生活中的凡人琐事,表述得跌宕起伏,让人们读得津津有味。他并不着意渲染情感,制造煽情的场景,更拒绝泡制刺激感官的段子,迎合低俗的猎奇欲望;他只是娓娓细数人和命运交手的一招一式。语句明白晓畅,不借用欧化句式的格言警句装饰和炫耀,只选择平常日子的浮光片羽,如此这般摆放一番,居然能以独特的视角,借小说主人公的遭遇,反射人生的哲理。 小说家功力的高下,显示在自己讲故事的方式中。所谓艺术造诣,或许就是有能耐将生活中的凡人琐事,表述得跌宕起伏,让人们读得津津有味。他并不着意渲染情感,制造煽情的场景,更拒绝泡制刺激感官的段子,迎合低俗的猎奇欲望;他只是娓娓细数人和命运交手的一招一式。语句明白晓畅,不借用欧化句式的格言警句装饰和炫耀,只选择平常日子的浮光片羽,如此这般摆放一番,居然能以独特的视角,借小说主人公的遭遇,反射人生的哲理。
长篇小说《正常人》就是这样。这书名平淡,毫无挑逗读者眼球的张狂。作家沈善增的笔墨,游弋在弄堂、石库门、崇明岛之间,自叙“我”——小说主人公如何从少年成长为男子汉的那段岁月。
煤球炉、八仙桌、铅桶、木盆、固齿灵牙膏和明星牌花露水……次第登场,纤毫毕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上海一个石库门内统厢房的容貌。“我”——绰号“老嘎”的中学生的生存环境,及其个人隐私的写实镜头,在《正常人》开卷伊始,就这样清晰曝光。它们类似巴尔扎克《人间戏剧》的细节描摹,以静制动,诱发在那个时代生活过的上海人的思绪。唤醒的记忆如同陈年水渍洇没留下的印记一样,弥散、氤氲着沧桑感。让读者感同身受小说故事场景的,还有《正常人》的语言。那些有着强烈方言色彩的词汇:“凉飕飕”的感觉、“薄嚣嚣”的嘴唇、“介晏”回来、“鉴貌辨色”……散发着上海滩市民生活的味道。它们都受命于作者的调遣,贴身紧逼那个时代的生活片段。如生活中真实的人一般,《正常人》中虚构的人物也都是有影子的,那些沪语腔调浓重的话语使它们成为他们,鲜蹦活跳地在纸页上跃动着。同时也看出作者沈善增对“小说是语言的艺术”,有一种虔诚的追求。
“我”从中学毕业,赴崇明农场务农,后调回上海市区,谈恋爱娶妻生子,《正常人》的故事情节延伸在这个轨迹上。“我”的命运与同时代人北上黑龙江、南下云南等经历相比,并不算波澜起伏,但是《正常人》却用不紧不慢的节奏,牵丝攀藤抓住读者,使人读着居然手不释卷。也许是得益于江南评弹的滋润,沈善增成功地借鉴了说书先生在琵琶三弦的琮铮声里,看似慢条斯理,却丝丝入扣的讲故事方式。《正常人》的字里行间,从容展示着那抓住听众的淡定自如。
少年成长为男子汉的题材,是西方经典文学中“成长小说”的传统主题。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高尔基的《人间》三部曲等数不胜数。近年来,连以小资招牌走红文坛的村上春树,也写了一部《海边的卡夫卡》,继续畅销。而诺贝尔文学奖获得主凯尔泰斯,在《无命运的人生》中,以回忆“集中营的幸福”而震惊文坛。这类作品开挖的是少年到成年的个人心理历程,以主人公面临社会遭际的陌生感和心理困惑,蔓延情节和展示社会。《正常人》与《大卫·科波菲尔》《人间》等的不同之处,在于“我”的自立,还面临社会价值观的急剧变幻。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解放前上海滩十里洋场的余韵、建国后翻身的新社会气氛、“造反有理”的极左思潮,此时正纠缠、交错,厮打得清浊难辨。连社会阅历丰富的中老年人都晕头转向,而“我”却要离家,独自面对社会。这时刻,“我”进行成人洗礼真是异常凶险。要知道在“文革”狂潮席卷的时候,一张报纸上领袖像的安置地位,都可能将一个“好人”立时三刻打成“现行反革命”,成为“坏人”。
学生的天真年代,认定“好”、“坏”的标准,是非此即彼。成人的成熟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明白世间人和事的复杂性,老托尔斯泰曾形象比喻说:“人如河流。河水都一样,到处相同,但是每一条河都是有的地方河床狭窄,水流湍急;有的地方河身宽阔,水流缓慢。有的地方河水清澈,有的地方河水混浊。有的地方河水冰冷,有的地方河水温暖。”社会如同一幅有多重层次、深浅不一的水墨画。优秀的成长小说就是让读者与主人公一起透视世间人事这幅水墨画的浓淡,《正常人》同时又显现出励志意义的独特光泽。
《正常人》中,从上海弄堂、石库门到崇明农场这条路弯弯曲曲,“我”歪歪斜斜地行走着。通过“我”的所见所闻,蜿蜒展示了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上海滩的世俗风情。正如美国著名作家索尔·贝娄所言:“小说家是一个想象力丰富的历史学家,他能比社会学家更逼近当代的事实真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