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逻辑》给我的最大启迪,就是黑格尔有关知性问题的论述。这些论证精辟的文字对我的思想起了极大的解放作用。因为知性的分析方法,长期被视为权威理论,恐怕至今还有人在奉行不渝。它使我认识到,自康德以来的德国古典哲学把知性作为认识的一种性能和一个环节是完全必要的。这可以纠正我们按照习惯把认识分为感性和理性两类,以为前者是对于事物的片面的、现象的、外在联系的认识,而后者是对于事物的全面的、本质的和内在联系的认识。按照这种两分法,我们就很难将知性放到正确的位置上,甚至还可能把它和理性混为一谈。知性和理性虽然都是对于感性事物的抽象,但两者区别极大。知性具有形而上学的性质,并不可能达到对事物的全面的、本质的和内在联系的认识。我们应该重新考虑德国古典哲学的说法,用感性—知性—理性的三段式去代替有着明显缺陷的感性—理性的两段式。那时我在隔离中,虽然前途茫茫,命运未卜,却第一次由于思想从多年不敢质疑的权威理论中解放出来,而领受了从内心迸发出来的欢乐,这是凡有过同样思想经历的人都会体会到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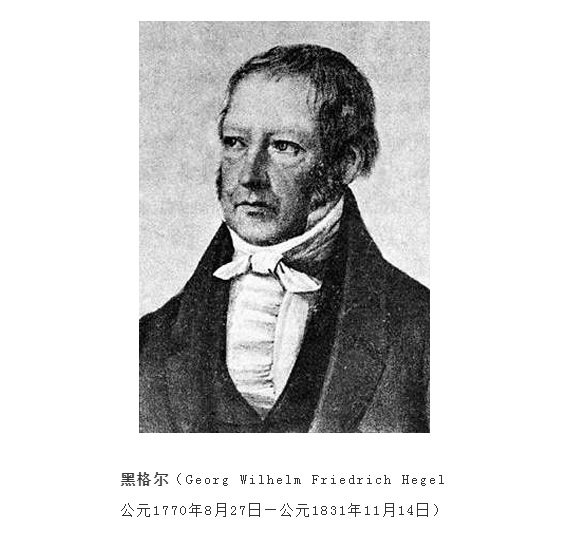
一九八三年初,我们在天津迎宾馆为周扬起草那篇惹起一场风波的讲话稿时,他听到我对知性问题的阐释很感兴趣,坚持要我在讲话稿中把这问题写进去。我说在此以前我已有文章谈过了,他说没有关系,可以在讲话稿中说明他对这观点的赞同。这篇讲话稿后来成为引发一次事件的开端。在这次事件中,知性问题虽然不是主要的批判对象,但也受到株连,被指摘为和权威理论唱对台戏,“要回到康德去”。对于这种责备,我一直沉默着,现在也不准备回答。我只想对掌握意识形态大权的批判者提一个问题:为什么你们回避了我对“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诠释呢?要知道除非在这个问题上将我的论据论证驳倒,你们是不能稳操胜算的。
当时我对于《小逻辑》所提出的三范畴即普遍性、特殊性与个体性的理论最为服膺。恩格斯曾说这三个范畴始终贯穿并运动在黑格尔的逻辑学中,他对此甚为赞赏。在黑格尔那里,这三个范畴是紧密相连不可分割的。普遍性是自我同一的,又包含特殊性和个体性在内。特殊的即相异,或有特殊性格,又必须了解为它自身是普遍的并具有个体性。个体性为主体和基本,包含有种和类于其自身,并具有实质的存在。黑格尔认为任何事物都是一个推论,就是说明一切事物都包含这三个环节于自身之内。后来我读了黑格尔《美学》,发现他在《理想的定性》中阐述理念经过自我发展过程而形成具体的艺术作品,就是按照上述三环节的理论加以论证的。后来我曾经撰写过一篇题为《情况—情境—情节》的文章,论述黑格尔的上述美学观点,现收入《清园论学集》中。美学中所说的情况相当于逻辑学总念论三范畴中的普遍性,情境相当于特殊性,情节相当于个体性。艺术家在创作活动中可以将情况、情境、情节中的任何一个作为中项或中介来带动其他两项。就《美学》中的这个例子来看,我更理解了黑格尔所说的“一切事物都是一个推论”这句话的合理性。
最近我在文章中常涉及黑格尔,只是想清理自己的思想,就自己受到黑格尔影响的那些观点,进行剖析,提出新的认识。这些年我几次在文章中提到逻辑和历史的一致性,就因为过去我对这个问题十分信服。六十年代,我曾向一位研究精神病理学的周玉常医生请教人的生长过程。在他的帮助下,我认识到从受精卵到胎儿,几乎在大致上重复了从动物到人的进化史,即由单细胞生物发展到高级动物的生命史。我又从阅读中知道,可以从不同年龄的儿童的认识过程(有人曾把这一过程分为特化阶段—泛化阶段—分化阶段—概括化阶段四个时期),来探讨早期人类的认识史。我以为这些事例都可以作为历史与逻辑一致性的佐证,从而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可信的研究方法。比如我们如果要知道概念是怎样在人的认识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或美感怎样在人的认识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我们只要注意对婴儿的观察,记录他们在不同发育成长阶段的认识活动或意识活动,就可以测知大概近似的情况了。我还发现,黑格尔本人的著作也是根据逻辑与历史一致性的原则来构成整体的框架的。不仅《逻辑学》、《美学》、《哲学史讲演录》、《精神现象学》各书如此,而且我们还可以将《小逻辑》和《哲学史讲演录》加以对勘来读。因为在逻辑学中,各个概念出现的程序,正是和哲学史上各个概念出现的程序同步的、一致的。这些理论上的思考和发现,使我对黑格尔提出的这一原则深信不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