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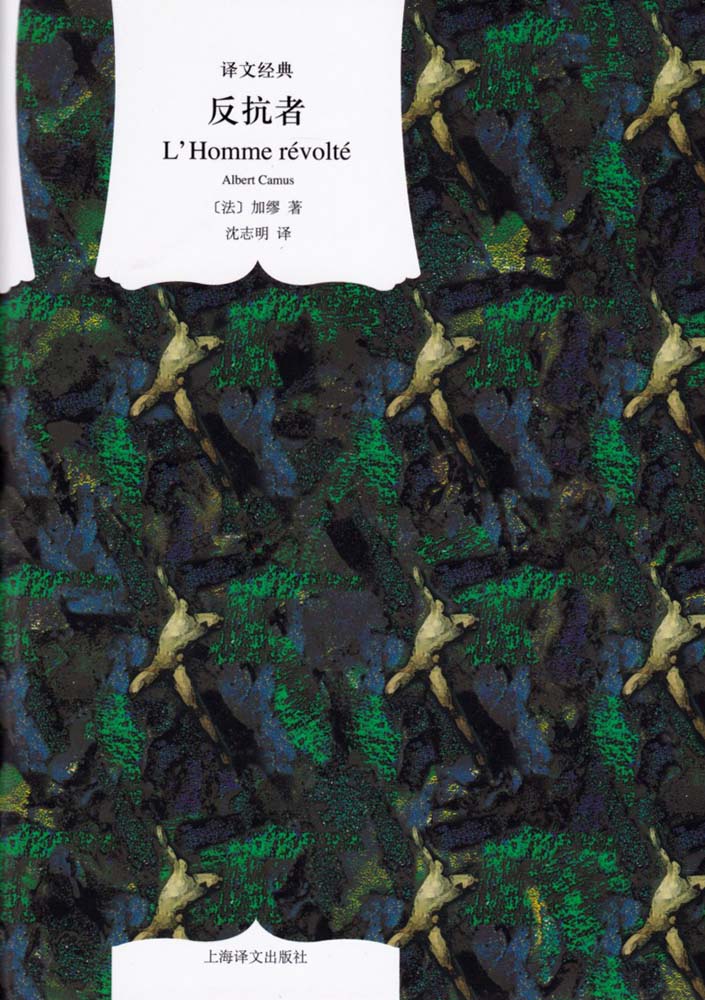 何谓反抗者?加缪指出,所谓反抗者,起步时,是个体反抗者。他首先说“不”,是拒绝而非弃绝,但他也是个说“是”的人。这个“不”,意味着一条边界线的存在,否则就越出自己的权限了。说到底,边界线奠定权限。这样,反抗者既肯定边界线,又掌握一切并将其维系在边界以内,就是他自我肯定拥有某种价值。于是向这个世界说“不”,向其本质的荒诞性说“不”,向威胁世人的抽象概念说“不”,向别人为我们准备的死亡文化说“不”。 何谓反抗者?加缪指出,所谓反抗者,起步时,是个体反抗者。他首先说“不”,是拒绝而非弃绝,但他也是个说“是”的人。这个“不”,意味着一条边界线的存在,否则就越出自己的权限了。说到底,边界线奠定权限。这样,反抗者既肯定边界线,又掌握一切并将其维系在边界以内,就是他自我肯定拥有某种价值。于是向这个世界说“不”,向其本质的荒诞性说“不”,向威胁世人的抽象概念说“不”,向别人为我们准备的死亡文化说“不”。
反抗者诉求什么?诉求相对的自由与相对的反抗权利。其实,反抗者根本不诉求完全自由,与之相反,谴责完全自由,并非质疑无限权力,而且允许高高在上者践踏被禁止的界线。反抗者远非诉求普遍独立性,而要求大家承认,只要有人存在的地方,自由有其自由的限制,此限制恰恰就是此人有反抗的权利。反抗之不妥协性的深远道理就在于此。但反抗者以另一种名义肯定完全自由不可能性的同时,要为自身索求相对自由,条件是守本分:“以人的身材高度对话比站在孤零零山峰上独自一人发布极权宗教福音的代价要低得多”,加缪如是说。
因此,反抗的问题跟个体概念的衍变紧密联系在一起,世俗中人,在人的观念中不断觉醒的同时,对自己的权利具有广泛的意识,故而反抗是有识之士的特性。加缪凭自己一生经历,逐渐发现悖逆天理、去神化能体现反抗的作用,于是下结论:“世人通过去神化逐步肯定自己,但永无止境。”个体反抗毕竟想要有自己的自由。
何谓个体反抗?西西弗就是个体反抗的典型,他以否认诸神和推举岩石这一至高无上的忠诚来诲人警世,在没有救世主的尘世上,正如伊壁鸠鲁所言:“我们等待复等待,消耗自己的生命,必将操劳过度而死亡。”西西弗身负重荷,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他推举的岩石,每个细粒都披着一道道矿物的光芒,与他本人融合一体了,心里非常充实。这种拼搏本身就是反抗:“他反抗,故他存在”,因为西西弗已成为物质,返回元素了:“实有就是石头”,“就是没有痛苦”,甚至变成“奇特的快感”,即“石头的幸福”,伊壁鸠鲁的结论是:“应当想像西西弗是幸福的。”西西弗式的个人反抗特征:“人生一半在欲语还休,扭头不看和沉默寡言中度过”,加缪如是说,并加添道:“一个沉默多于说话的人是一个更有价值的人。”
上天真福者们必定认为,西西弗的“我反抗,故我存在”是在刷存在感,确切说是在刷荒诞存在感,因为人的生命“要么上天,要么入地”。概率论者对未来现实许下的诺言越大,人的生命价值就越小,极而言之,一文不值。他们的至福最大源泉是观赏古罗马皇帝们在地狱备受煎熬的场面,这种至福,很遗憾,也是正直的世人们去观看砍头处决的那种快乐,用鲁迅的话来说,用馒头蘸砍头鲜血的乐趣。
那么,反抗的本原究竟是什么?其实,反抗的本原仅限于拒绝屈辱,并且不要求别人受屈辱,甚至肯接受为之承受痛苦,只要正直得到尊重就行。总之,加缪接受或至少参照施蒂纳的主题思想,现概括如下: 个体是一切价值、一切思想、一切行为的起源。什么上帝、人类、人民、真理、自由,不过是抽象的概念而已。利己主义否定所有其他利益,而最好的利己主义莫过于有利于个体自身的利己主义: 只顾自己不顾别人。因为,大写的“我”是“独善其身”者,即世人取之不尽的虚无。这一绝对个体主义的原则是该书的主题之一:“独善其身者”就是辩证思想的一个极端,即虚无的另一端,可理解为“存在”,所以大写的“我”是存在的主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