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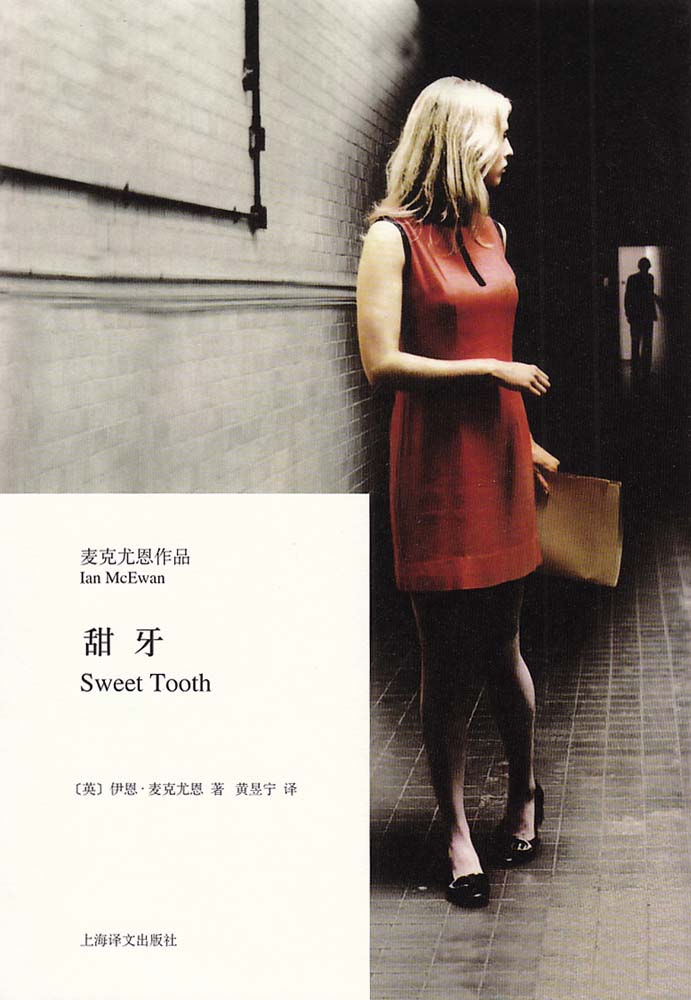 像麦克尤恩近年来的其他小说一样,《甜牙》也是那种情节与其所处的时代咬合得格外紧密的作品。表层的第一人称叙述者是一位出身教会保守家庭,在剑桥读书时又被年长她一倍的情人招募到军情五处的女特工。尽管塞丽娜只是职位最低且倍受女性歧视政策压制的文职助理(五处的不成文共识是:女人守不住秘密),她仍比一般的女性更有条件叙述英国七年代的整体状况,毋宁说是腹背受敌的社会困境—冷战意识大面积渗入普通人的生活,爱尔兰共和军的恐怖活动和全国性罢工运动此起彼伏,中东危机导致能源匮乏,嬉皮士运动退潮,将一大批精神幻灭、身体困倦的青年扔在了沙滩上。 像麦克尤恩近年来的其他小说一样,《甜牙》也是那种情节与其所处的时代咬合得格外紧密的作品。表层的第一人称叙述者是一位出身教会保守家庭,在剑桥读书时又被年长她一倍的情人招募到军情五处的女特工。尽管塞丽娜只是职位最低且倍受女性歧视政策压制的文职助理(五处的不成文共识是:女人守不住秘密),她仍比一般的女性更有条件叙述英国七年代的整体状况,毋宁说是腹背受敌的社会困境—冷战意识大面积渗入普通人的生活,爱尔兰共和军的恐怖活动和全国性罢工运动此起彼伏,中东危机导致能源匮乏,嬉皮士运动退潮,将一大批精神幻灭、身体困倦的青年扔在了沙滩上。
总体上,《甜牙》中有关七年代的描写,调子远比《在切瑟尔海滩》中的六年代更灰暗更压抑,更洋溢着“无力挣脱只能就范”的失重感。
《甜牙》对于间谍世界的展示,刻意与老套程式中的“谍战”拉开距离,我们看不到神秘的、大规模的智力游戏,只有琐碎可笑、被一整套官僚主义和机构内卷化效应拖得一步一喘的办公室政治。无论是一份理由暧昧的密控档案,一篇只消上级一个眼神就推倒主旨的报告,还是一位因为个性张扬就遭到解雇的女职员(塞丽娜的闺蜜),都折射着某种早已被习以为常的荒诞性。甚至“甜牙行动”本身,究其实质,不过是在冷战处于胶着期时,五处与六处对日渐紧张的资源的争夺,以及英国特工机构与财大气粗的美国中情局之间微妙关系的曲折反映而已。按照汤姆恍然大悟后的说法,“这是在发疯。这是那些特务官僚机构让自己一直有活干的办法。不晓得哪个妄自尊大的年轻人,怀揣暧昧的梦想,拿出这条诡计取悦他的上级。可是谁也不知道这样做有什么目的,有什么意义。甚至没人会问。这真够卡夫卡的。”
作为“文学”与“谍战”的特殊“嫁接”形式,“甜牙行动”当然不是无本之木。英国文学圈与政治素来深厚的关系,英国小说界与间谍业之间素来纠结的瓜葛(我们熟悉的毛姆、格林,弗莱明和勒卡雷之类,都是著名的“跨界”人物),均可视为《甜牙》的灵感源泉。更直接触发麦克尤恩写作动机的是近年来不断解密的关于“软性冷战”的档案,其中既有英国外交部情报司对乔治·奥威尔的作品《一九八四》和《动物农庄》的全球性推广,也包括中情局对《日瓦戈医生》及《邂逅》杂志的资助。
基于以上背景,我们就可以理解《甜牙》与典型的间谍小说之间,究竟有多大程度的不同(当然,这仅仅是“不同”之一)。尽管麦克尤恩对间谍小说有浓厚的兴趣,并且多次在访谈中宣称英国文坛欠约翰·勒卡雷一个布克奖,但你如果纯粹以勒卡雷式的间谍小说标准来衡量《甜牙》,恐怕会怅然若失。话说回来,从《最初的爱情,最后的仪式》到《追日》,麦克尤恩什么时候给过我们意料之中的,纯粹而表象的东西?哪一次我们不需要费力拨开表面的蛛网,才能窥见作者的用心?
至少有一部分用心,是揭示人,尤其是知识分子保持思维独立、心灵自由的困难—这种困难往往潜移默化,钝刀磨人,最后让“初心”变成一个惨淡的笑话。当你以为你获得了自由,当你以为在用自己的脑子思考时,恰恰可能是你走入囚牢的开始。把这个无形囚牢的外延扩大,几乎可以把整个世界装进去。一如既往地,麦克尤恩并不让作者的立场干涉读者的视角,最大程度地克制了在意识形态问题上跳出来评判是非的冲动。毕竟,在并不算太长的篇幅里,通过有限的视角,将历史政治揉碎后编入生活细节的能力,以及对于泛政治的社会生活的复杂性的全景展示,是麦克尤恩一向擅长的绝活。
就像大部分读者在前半段就能猜到的那样,汤姆和塞丽娜相爱了。爱得步步为营,爱得亦真亦假,爱得绝处逢生。即使不揭开结尾的玄机,未曾感受到关键性的逆转给这段感情增加的冲击力,我们也足以通过前二十一章体会其复杂、细腻与吊诡。对结构敏感一些的读者,还能在读到总页数的一半时,从汤姆创作的小说《逢“床”做戏》中若有所悟—没错,你确实可以把这个故事看成是对整部小说,或者是对汤姆和塞丽娜的“整个爱情”的隐喻。从读书到阅人,从俘获到被俘获,从完成任务到摧毁任务,从欺骗到被欺骗,这些因素到了麦克尤恩笔下,成了丝丝入扣、令人信服的情感催化剂。
“过于娴熟的技术导致真实的情感力量缺失”是近年来麦克尤恩的作品常常会被人扣上的帽子,但在我看来,《甜牙》是个例外。当汤姆和塞丽娜的情感被置于角度复杂的棱镜中时,当 “真实”不再像许多传统小说那样具有惟一的维度时,《甜牙》在很多章节(尤其是下半部)中的情感力量饱满到几乎要溢出来的地步,让我在翻译的过程中几度为之深深感动。《甜牙》中引用过奥登的名作《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其实,如果拿奥登的另一首短诗形容汤姆与塞丽娜的爱情,也格外恰切。那首诗写于一九二八年,标题是“间谍”,但经过考证,它却是一首借间谍的意象表达思慕爱人的情诗:“……黑暗中,被奔腾的水流声吵醒,他常为已然梦见的一个同伴,将夜晚责备。他们会开枪,理所当然,轻易就将从未会合的两人拆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