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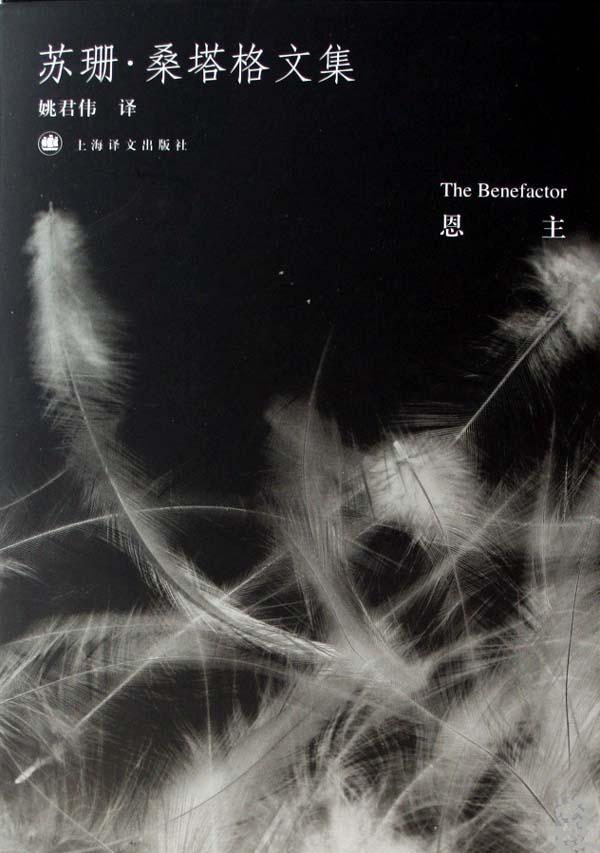 在看桑塔格的《恩主》之前,我一直有一个模糊而又自以为正确的看法,那就是一个人如果过度关注眼前的现实,关注这个纷纷扰扰的世界,他是不可能写出一部深入内心的作品的。最现成的例子就是李敖,没有人敢否认他的博学,他的强悍,他在黑暗的现实面前斗争的勇气,但他的小说《北京法源寺》、《上山、上山、爱》除了让人再一次见证他的博学,实在算不上好的小说。 在看桑塔格的《恩主》之前,我一直有一个模糊而又自以为正确的看法,那就是一个人如果过度关注眼前的现实,关注这个纷纷扰扰的世界,他是不可能写出一部深入内心的作品的。最现成的例子就是李敖,没有人敢否认他的博学,他的强悍,他在黑暗的现实面前斗争的勇气,但他的小说《北京法源寺》、《上山、上山、爱》除了让人再一次见证他的博学,实在算不上好的小说。
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 1933年—2004年)被誉为“美国公众的良心”,与西蒙·波伏娃、汉娜·阿伦特被并称为西方当代最重要的女知识分子,那些为她赢得广泛声誉的也是那些评论文章(就是没读过她作品的人也知道她那本《反对阐释》),她曾经满世界的跑,许多地方当时正战火纷飞(比如越南,比如前南斯拉夫),很难想象,她这样的一个作家能写出一部深入人的内心的小说。但她偏偏就写出这么一部小说,我们只能说她比我们想象的更为丰富,更多面,也更为有才能,她的才能和丰富总会打破我们的一些惯性思维。
桑塔格写《恩主》那一年(1963年)刚好三十岁,那是个从青春期以来一些迷茫和困惑还没有彻底解决的年纪,桑塔格不想把这种困惑带到四十岁,她要把它们打发掉,我相信这是她的写作动机。尽管桑塔格说,她的第一本小说一点也不想写她自己,但我坚信,许多人的第一本小说,多多少少都会是自己的精神自传,无论他给他小说里的主人公带了什么样的面具,也无论他的主人公与他有多么不同的人生经历。我看了许多对于《恩主》的评论,没有哪个人的评论比桑塔格对自己的作品的评论更为准确的了:“《恩主》探讨某种遁世的天性,事实上是非常虚无主义的———一种温柔的虚无主义。”其实探讨的还有死亡,而谁都知道,死是彻底的虚无。
这种无限遁世的可能被桑塔格安排一个法国男人希波赖特来承担——开始是一个早早赢得声誉的大学生,最后是一个躲在一间空荡荡的屋子里偶做些善事的老男人。这个男人起先偶尔做了一个离奇的梦,然后是一个又一个离奇的梦,他对梦里所呈现的景象不能理解,然后不停地自我审视,从而陷入自我的泥潭不能自拨。他的梦又有意无意的与他的现实生活发生了“互动”,这种体验,几千年前的庄子曾经体验过。他曾就他的梦给他带来的困惑求教于他的作家朋友让.雅克,就教于他的相好安德斯太太,求教于神父,求教于一个研究秘密宗教的教授,但没有哪个人能给他解开困惑。
而在现实生活中,希波赖特的基本姿态是逃离,最最主要的是逃离安德斯,先是于一次蜜月似的旅行中,把她以一万三千法朗买给了一个阿拉伯人,安德斯太太逃回首都(谁都知道那是巴黎)之后,他不惜纵火杀人来摆脱她,杀人不成之后,又匆忙结婚,事后为了良心上的安宁,送了她一幢装璜得很豪华的房子,及时来的战争彻底击垮了安德斯夫人,而在结尾处出现的另外一位安德斯夫人,虽然没有再纠缠他,但却给了他一段梦靥般的恐惧,我们弄不清希波赖特是因为崩溃而最终走向了平静,还是因为顿悟而走向了平静,还是因为筋疲力尽而平静,一切都是是而非。最后的几个章节几后又把前面的现实经历都变成了梦,而把梦又变成了现实,庄生梦碟重演了一次。
有人把桑塔格称为女权主义者,我觉得那实在是对桑塔格的一种误读,最少对于《恩主》的作者桑塔格如此。在《恩主》中,里面出现的女人多少都有些可笑,而男人因为那天然的本性而给她们造成了伤害多少有些可恶,但这种可恶,甚至连张爱玲说的“小奸小坏”都谈不上,只是他们就是那样。
还有人把桑塔格归于先锋作家,但从《恩主》看,她并没有玩弄那些让人头晕目旋的文学技巧。我相信她三十岁的时候已经很博学,但在小说里,我好象没有看到一个书名号,也没有提到任何一位大师的名字以及他的名言,倒是《恩主》本身里面有许多称得上名言,比如:
“尽管我拼命往前冲,我依旧跳不出自己的意识外围线,但是,我却能进入更里层。我能够在大圈中找到一个小些的圈子,然后爬进去。”
“如果我不能走出自我,我就待在其中。我会抬眼看着自己,把我视为自己的风景。”
有兴趣的读者,还可以找到许多适合自己的经典的句子。
而在小说的结尾那段内心独白,只有真正的沉溺最后走向平静者,才会说出那样的独白。如果把这段文字放在佩索阿的《惶然录》里,我一点也不会觉得唐突。
桑塔格于2004年底去世,不知她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是不是那样平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