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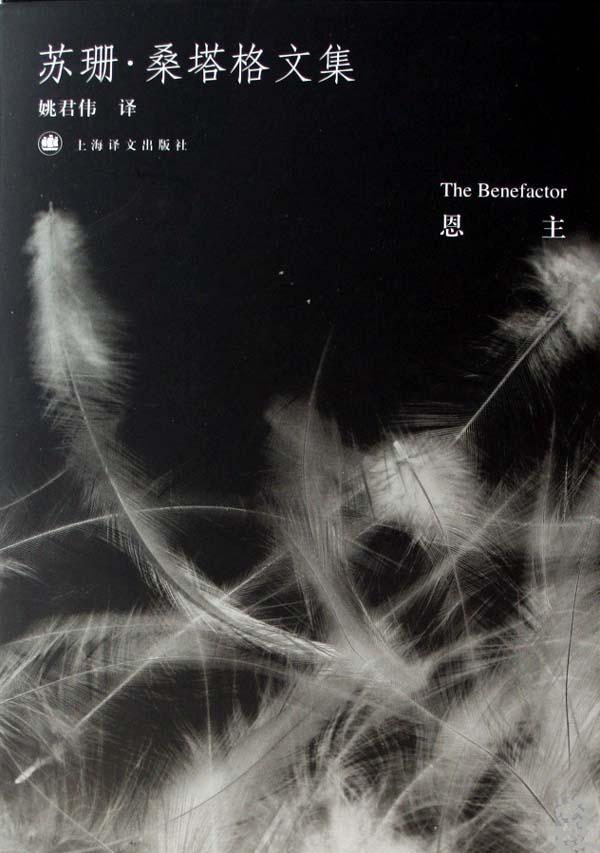 女友哈丽雅特的出现打消了她对感情的顾虑,解放了她的情欲,让她开始正视自己的同性倾向,也让她对自我的人生重新定位,所谓“重生”正是从此开始。 女友哈丽雅特的出现打消了她对感情的顾虑,解放了她的情欲,让她开始正视自己的同性倾向,也让她对自我的人生重新定位,所谓“重生”正是从此开始。
1957年12月底,桑塔格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日记是用来表现我个性的工具。它代表我是一个在情感和精神上都是独立自主的人。因此(唉),它根本不是单纯记录我的每天的真实生活,而是——有许多则日记正是如此——提供了与我实际生活不同的其他可能性。”其时桑塔格24岁,已婚,一子,远在巴黎留学,正陷入一种不可自拔的感情漩涡,对方是她早年的好友哈丽雅特。
桑塔格与哈丽雅特最早结识于1949年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大卫·瑞夫编选了他母亲桑塔格日记的第一部分,并命名为《重生》,这个书名正是源于那个时期桑塔格的百般挣扎的情感经验。在认识哈丽雅特之前,桑塔格正经历一个迷惘期,她能察觉到自我的天赋,但是对以后人生的方向并不确定,在两性关系上尤其困扰。在1949年4月9日的日记中,她记下了与某位男生的交往:“一想到和男人有肉体关系,我只有羞辱堕落的感觉——第一次亲吻他——长长的一吻——这念头很清楚地冒出来:‘就是这样吗?好蠢啊。’”她羞于提及对男性的厌恶和对同性的爱慕。某种程度上,哈丽雅特的出现打消了她对感情的顾虑,解放了她的情欲,让她开始正视自己的同性倾向,也让她对自我的人生重新定位,所谓“重生”正是从此开始。
1949年5月26日的日记中,她这样写道:“我带着崭新的双眼,重新审视我的世界。其中最叫我惊恐的是,我竟然让自己埋首于学术生活中。对我来说这毫不费功夫……只要成绩优异,继续念硕士,当助教,找些没人有兴趣的冷僻主题写几篇论文,熬到60岁,然后成为又老又丑但受人敬重的专职教授。为何我的人生要这样过?”她开始意识到她的生活从此有所不同,因为她知道该去做什么,她知道了她的身体充满情欲,她知道她这样的身体热情并不羞耻,她知道想去追求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尽情享受肉体和情欲的欢愉,体验和享受人生,但在一个更高的精神层面上绝不放弃对智性生活的追求。“一切就从现在开始——我重生了”。
《重生》是桑塔格日记的第一部分,截取的是1947—1963年桑塔格早年的生活片断。她曾在日记中写到,日记的功能之一就是被人偷看的,“让那些在日记中才能诚实相对的人”。写下这句话时,她偷看了哈丽雅特的日记,了解到哈丽雅特对她的评价草率,苛刻,充满恶意,这种来自爱人的想法让她很受伤。我们通过那些充满睿智的见解,深刻的洞见,咄咄逼人的气势的文化批评和论文中得到桑塔格的印象在这本日记中得到了颠覆性的印证。这是任何一个少女都会经历的彷徨期,对未来的不确定,对感情的妥协,对肉体和情欲的沉迷,让我们意识到这位伟大的女性同样有着极为私人的一面。她经历了离婚,独自抚养大卫·瑞夫,与哈丽雅特的感情最终崩溃,而后又陷入到另外一份感情中,但是这段感情的经历同样糟糕,给人的印象,她和她的那些爱人们似乎只有通过互相折磨才能相爱,“虐待、敌意是爱情里的主要成分。因此,要牢记住重点:爱是彼此敌意的交换。”我们每个人都会经历一个爱情挫折的阶段,这种受挫很大部分源于爱人之间彼此熟悉乃至厌恶,但最终却无法分离,于是只能通过互相折磨对方才能找到相爱的感觉。
但是,有一个很是怪异的转折点。我们为什么读桑塔格的日记呢,我们偷窥她的隐私难道就是为了看到“她是一个弱女子”么?我们所期待的是那个有着耀眼的光环,绝世的才情,明星般美貌,那个强势、傲慢,才华横溢,咄咄逼人,却总能让我辈叹服不已的女人。我们渴望从中窥探她是如何从一个不谙世事的少女成长为特立独行睥睨天下的伟大作者。除了与生俱来的天赋,难道我们不想知道桑塔格是如何炼成的么?
在日记中,除了那些剪不断的情事纠缠,也许我们更为渴望看到她自我写作的觉醒吧。但是当我意识到了她的觉醒之后,突然觉得这样的“重生”方式很是怪异。在1959年11月19日的日记中,她如此记录她开始渴望写作:“性高潮让我整个心思聚集,我开始渴望写作。性高潮的体会不是救赎,更重要的是自我的诞生。我无法书写,直到找到自我。我唯一想成为的作家,就是那种暴露自己……写作就是消耗自己,赌上自己……”我之所以觉得桑塔格从感情到书写的转换之间有种怪异的联系,是因为她觉得这种书写渴望与她的同性恋身份有关,“我需要有个认同的身份当武器,来反击社会对我的敌视”。
如果不是读这本日记,我无法相信这种书写理论,从自我身份的认同中找寻一种写作的使命感,这种意识很多写作者都会具备,但是在桑塔格的一生中,她从未真正承认过她的同性恋身份。尤其在上世纪80年代,女性解放运动风起云涌,桑塔格又有着如日中天的知识分子身份,很多女性人群希望她能大胆承认同性恋身份,从而为女性解放运动添一份力,但是桑塔格始终闭口不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