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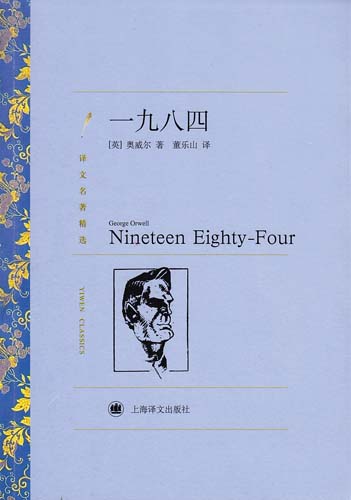 翻阅奥威尔的《战时广播》和《战时评论》两本书,中国——这个对于奥威尔遥远而陌生的国度,在他的心目中占据一个重要位置。 翻阅奥威尔的《战时广播》和《战时评论》两本书,中国——这个对于奥威尔遥远而陌生的国度,在他的心目中占据一个重要位置。
《战时广播》分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收录奥威尔在BBC期间所撰写和编播的广播谈话;第二部分,收录同一期间围绕这些广播,奥威尔与文化界有关人士的大量来往信件。奥威尔的这些广播谈话,大多与文学有关,分专题向东方听众介绍欧美文学。与他来往通信的则是同时代的英国著名作家,如福斯特、艾略特、威尔斯等。《战时评论》所收内容,全部是奥威尔从一九四一年底到一九四三年初撰写的“每周战事评述”。这些评述,大多数由他本人广播。这些战事的评述,给人们留下了极其珍贵的历史资料,也使我们可以深切地感受到一个作家面临人类浩劫时的复杂心情。
奥威尔不是政治家,更不是军事家,但他对中国的抗战,却似乎具有一种世界性的战略眼光,在随后一年多的战事评述中,他总是立足于整个世界战事的全局来分析东方的战争。同时,他也清醒地认识到这是一场持久的、艰苦的战争,对远在东方的中国人民寄予充分的理解、同情和支持。
令人感动的是,奥威尔一直坚信日本侵略者在中国、在太平洋战争中最终必然失败,不管在评论中国战事还是其他东方战场的现状时,他总是以一种钦佩和理解的口吻,谈及中国人民。这不仅表现出这位英国作家的人道主义精神,也反映出他的客观、公正的现实主义态度,没有丝毫的贵族气息,没有丝毫的所谓“西方人的傲慢”。可以说,他是真正将中国人置于一个与世界所有国家相平等的地位来加以谈论的。在《战时评论》一书中,我们随时可以看到类似的论述。
一九四二年五月十六日,奥威尔写下一大段对总的战争局势的分析,其中关于中国部分的议论,更加集中地表明奥威尔与中国人民的情感。
这段议论中,有相当篇幅的文字,在审定时大概因为违反当时英国政府的一些观点而被删除。幸好作为档案它们被保留下来,保持了奥威尔讲稿的历史原貌。
我们无从得知,当这些倾注着奥威尔热情的文字被迫删除时,他会有一种什么样的心情。但可以肯定,类似的、几乎每天在B B C都会遇到的经历,必然要使他承受巨大的精神折磨和痛苦。他是一个极其厌恶强权专制政治的自由主义者,所追求的是人格的完善和思想的自由。一九四八年在创作小说《一九八四》时,主人公温斯顿·史密斯的工作状况,无疑有奥威尔本人在B B C工作的影子。史密斯所在的部门,名为真理部,负责新闻、娱乐、教育等,但是,史密斯的工作却是整天编造谎言,修改谎言,涂抹历史或者人的记忆。奥威尔研究者便认为,奥威尔对所谓真理部的描写,得益于他的BBC的工作体验。我想,他所写的“每周战事评述”不断被删改,必然会深深刺痛他的心,在他的感情深处笼上浓重的阴影。不能按照一个作家自己的理想和思考来报道和评论中国的抗战,不能生活在他所追求的理想环境中,而只能让政治或其他东西约束自己,这不能不是奥威尔在BBC遇到的令人烦恼的精神折磨,显然,它无形之中影响了奥威尔的创作。
奥威尔与中国之间的短暂关系,会引发出这样的话题,想必是那些删改者始料不及的。
阅读与摘译奥威尔两本书的时候,恰是我与董乐山先生来往频繁之际。我们住得很近,探望他,请教翻译问题,帮他编辑随笔集,约他写回忆录,成了九十年代我们之间交往的重要内容。记得我将上面这段文字拿起请他看,他也认为奥威尔在B B C期间的讲稿多次被删改,以及在B B C工作的经历,应该为创作《一九八四》提供了很好的素材,包括史密斯的工作环境、气氛、方式等。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没有B B C的经历,或许《一九八四》会是另外一种构思。
在老一辈翻译家中,董乐山是我很敬重的对象。他的翻译对读者的冲击,不只是限于在翻译的信、达、雅方面所达到的高度,更在于他把翻译的选择,作为履行一个知识分子历史责任的方式。岁月的磨砺,早早地让他变得成熟而深沉。他不是那种逆来顺受的弱者,也不是思想浅薄随遇而安的庸碌之辈。他知道智慧与知识对一个知识分子所具备的意义,他更知道如何在有限的空间里,放飞无限的思想和情感。他并不是随意地走在翻译的路上,漫不经心地顺手拿起一本书就动手翻译,仅仅把这作为打发时光消磨生命的一个过程。恰恰相反,他把翻译的选择,与对命运的感触、对历史的观照紧密联系在一起。当他最初决定动手翻译《第三帝国的兴亡》时,这种翻译与人生的关系便开始形成。八十年代初率先完成《一九八四》的翻译,从那时起,一直到他生前最后出版几本译著《西方人文主义传统》、《奥威尔文集》、《苏格拉底的审判》,他所翻译的各种不同的史著、回忆录、小说、理论著作,与他的所有书评和杂文,构成了一个整体,将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在当代中国所发挥的独特作用表现得美丽无比。他的思想在发出自己的声音,从而,他的文章和他的译著便具备了持久的生命力,而且不会因他去世而为人淡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