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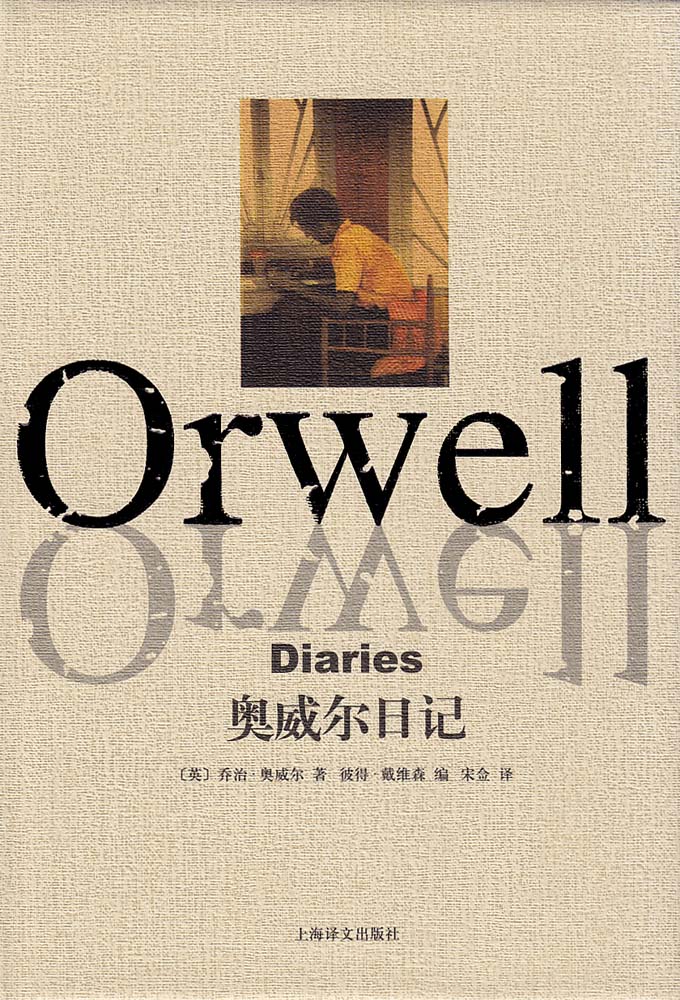 乔治·奥威尔曾在评论超现实主义画家达利的文章中宣称:“自传只有在揭示丑陋真相时才是可信的。那些对自己评价良好的人很可能是在撒谎,因为所有生命倘若从内部洞悉,都呈现为一系列的失败。”奥威尔如此激烈的反对自传,但是他的大部分作品,除了最为知名的《一九八四》和《动物农场》外,都表现出了一种强烈的自传性,第一人称叙事贯穿始终,大多数又是纪实性作品,就算偶尔变化叙事角度,也总是将自己的经历带入作品之中。他笔下的大多数主人公都是穷困潦倒,而且他对自己私生活讳莫如深,小心翼翼地不让自己陷入新闻报道之中。这种谨小慎微的性格,也让我们理解为何穷困了半辈子,当《动物农场》开始大卖之后,他偏偏选择了远离都市,隐居在一个小岛之上写作《一九八四》。 乔治·奥威尔曾在评论超现实主义画家达利的文章中宣称:“自传只有在揭示丑陋真相时才是可信的。那些对自己评价良好的人很可能是在撒谎,因为所有生命倘若从内部洞悉,都呈现为一系列的失败。”奥威尔如此激烈的反对自传,但是他的大部分作品,除了最为知名的《一九八四》和《动物农场》外,都表现出了一种强烈的自传性,第一人称叙事贯穿始终,大多数又是纪实性作品,就算偶尔变化叙事角度,也总是将自己的经历带入作品之中。他笔下的大多数主人公都是穷困潦倒,而且他对自己私生活讳莫如深,小心翼翼地不让自己陷入新闻报道之中。这种谨小慎微的性格,也让我们理解为何穷困了半辈子,当《动物农场》开始大卖之后,他偏偏选择了远离都市,隐居在一个小岛之上写作《一九八四》。
对大多数作家而言,日记是窥探一个作家私生活的最好方式。但对奥威尔而言,他的日记对私人记事寥寥无几,更多是提供写作的素材和时代的记录。所以这部由彼得 戴维斯编选的《奥威尔日记》记录最多的是一个小人物的贫困与大时代的政治。回想一下我们读过的大多数作家留下的日记,我们就能明白为何奥威尔的日记如此不同。日记具有强烈的秘密性和私人性,它描述的东西大多数不适合公开,涉及到作家的私生活只是一方面,更多时候充满了个人的偏见性书写,会给很多人带来麻烦。而且作家日记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他是出于作家本人之手,具有一种独一无二的秘密属性。但是在奥威尔的日记中,在不同的时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代写。
戴维斯在编选日记中总结说:“这些日记不是那种用代码写成的纯私人记录,而是大体上用平直的语言写成的他对生活、他对大自然的观察以及当时的政治事件的记录。当他在1939年9月离开沃林顿后,他的妻子艾琳帮他代写了家庭日记;1947-1948年的那个冬天在他住院期间,他的妹妹安维尔带他记录了一些基本的信息,如天气以及在巴恩尔农场周围开展的农务。”除了这些比较公开的时代纪录,奥威尔的日记还有一些值得注意的地方,比如他很少在日记中提及关于自己的写作和作品的评价,偶尔顺便提起,也是为了进行比较。从这些日记中,我们很少能够知道他喜欢什么类型的作家和行文风格。当然,这些都可以从他的那些知名的随笔文字中获得,但是对一个作家而言,记录自己写作形成过程是一个很自然的事情,奥威尔回避这种形式的书写,似乎源于一种对写作本体的怀疑,换句话说,写作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尤其是在战争年代,有比写作更重要的事情。
《奥威尔日记》中收录的日记从1931年8月截止到1949年9月生病去世前夕。奥威尔一生的经历很奇特,与大多数作家的那种不得已的穷困潦倒不同,他们一生都渴望通过写作进入上层社会,但是奥威尔从开始就有意识地步入最下层的生活。他出生于印度,得了一笔奖学金之后便到伊顿公学读书,之后在缅甸警局工作了五年,接着跟随一群流浪者在巴黎和伦敦过了一段落魄的生活,他也曾和威根的矿工住在一起,感染过肺结核,参加了西班牙内战并被射伤。他写过三部报告文学和四部小说,这些作品为他赢得了良好的声誉,却没能改善他的经济状况。战争的爆发使他一度无所适从,精神沮丧。那是他一生最为穷困潦倒的事情,由于身体欠佳,既不能参军,也找不到任何能让他对战争进点心力的工作。
战后他终于靠《动物农场》的畅销过上了稍微好的生活,他偏偏又选择了远离尘嚣的都市,去一个小岛上写作《一九八四》。这些悲惨的、痛苦的、纠结的经历都体现在这些日记中。日记开始时,他正准备去肯特郡摘啤酒花。奥威尔的一生都在实践这种贫困生活,这种不可思议的体验构成了奥威尔写作中的主要内容。我们无法理解这种生活,总是生活在贫困线之下,忍耐饥饿、严寒、羞辱和不公平的对待,但是他似乎乐此不疲。
美国的传记作家杰弗里 迈耶斯分析说奥威尔一生有一种自虐的心理需求,这种需求源于奥威尔的一种罪恶感,一种社会的原罪,他们越是远离人类痛苦的场景,自责的感受就愈加强烈,对他们而言,面对社会不公或政治专制时保持沉默是可耻的行为,是与邪恶同流合污的举动。为了缓解这种社会的原罪,奥威尔在缅甸辞去职务,为了补偿自己国家所犯下的政治罪恶而加入了巴黎和伦敦被压迫的穷人队伍中,他同这些人一起反抗暴君,成为普通人中的一员。奥威尔还通过创作式的驱魔来减轻自己的罪恶感。所以奥威尔的一生仿佛都可以解读成“为崇高事业而产生的受虐冲动,证明他为减轻自己的罪恶感而产生了自我惩罚的需求”。当然,尽管奥威尔有这种受虐倾向,他的创作也明显证明了他有能力超越这种个人的罪恶感,并将之有效地引向社会思想行为和政治思想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