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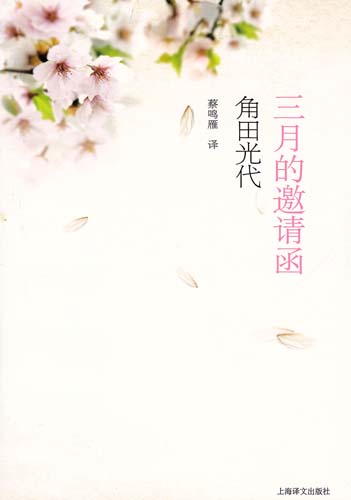 角田光代虽然不算极著名的日本作家,但中文世界的读者对她绝不陌生。她的著作如《礼物:一生中最珍贵的十二个礼物》、《对岸的她》、《沉睡在森林里的鱼》、《摇滚妈妈》、《三月的邀请函》及《空中庭园》等,都早已有中文简体版流传。把角田光代放在由“私小说”过渡至“风俗小说”的光谱中去理解,其实一点也不突兀。事实上,即使我们熟悉的村上春树,由1979年《听风的歌》及1980年《1973年的弹珠玩具》等满溢“私小说”风味的作品出发,也是到1982年的《寻羊的冒险》才进一步转向朝“风俗小说”作家的方向发展,简言之也是成为更畅销作家的“必经之路”。角田光代的畅销程度当然与村上春树大有差异,但其发展历程也不无暗合之处。 角田光代虽然不算极著名的日本作家,但中文世界的读者对她绝不陌生。她的著作如《礼物:一生中最珍贵的十二个礼物》、《对岸的她》、《沉睡在森林里的鱼》、《摇滚妈妈》、《三月的邀请函》及《空中庭园》等,都早已有中文简体版流传。把角田光代放在由“私小说”过渡至“风俗小说”的光谱中去理解,其实一点也不突兀。事实上,即使我们熟悉的村上春树,由1979年《听风的歌》及1980年《1973年的弹珠玩具》等满溢“私小说”风味的作品出发,也是到1982年的《寻羊的冒险》才进一步转向朝“风俗小说”作家的方向发展,简言之也是成为更畅销作家的“必经之路”。角田光代的畅销程度当然与村上春树大有差异,但其发展历程也不无暗合之处。
由“私小说”到“风俗小说”
絓秀实认为,从角田光代的履历看,她的统文学血统昭然若揭。1990年凭《寻找幸福的游戏》获海燕新人文学奖,1996年再凭《假寐之夜的UFO》获野间文艺新人奖,基本上奠定了角田光代于九十年代初期的纯文学作家的社会定位。而与此同时,她初期小说笔下的主人翁,不少都是自由工作者,当中也曲折地投射出角田自身的影子,视之为“私小说”系统的创作也无大偏差。但当《空中庭园》成为了2003年的直木奖候补后,继而在2005年以《对岸的她》获直木奖,正式宣示了她由统文学转化至“风俗小说”的范畴去。
“风俗小说”最基本的意思是指描述世相及风俗等社会现象的小说。部分字典上的说明也突出了它虽然具备强烈的风俗描写要素,但相对作者所带出的思想性一般较为稀薄,往往停留在表面的现实主义上,令作品存在局限。但回到角田光代,她的过渡不仅解放了“私小说”的狭隘局限,也把纯文学的意识引入了“风俗小说”的范畴内,令作为作者的她与作为通俗文类的“风俗小说”得到双赢的效果。
初期的文学性
角田光代早期的文学性的关键词是气氛。在1993年的《粉红巴士》中,女主角表面上好像是幸福的主妇,但自大学时期起,不断有与无家可归的露宿者密切联系的经验。从“私小说”的角度出发,1994年的《假寐之夜的UFO》及1997年的《草之巢》均属此类例子,而且她早期的很多其他小说,也有提及作为背包客出游东南亚一带的现实个人体验,当中尤以1995年的《真实之花》最为明晰。
文评家石川忠司认为,角田光代的小说时常弥漫着一种不稳定的疲劳感气息,小说中的主人翁往往呈现无力怠惰的状态,好像对眼前的一切均无力处理。事实上,在“私小说”的研究上,一些文论家如柄谷行人及山崎正和均曾点出,气氛才是“私小说”的主体,而非一般人以为的“私”——即主角自身。角田的纯文学特质,正好把持了“私小说”的核心价值,以气氛作为中心,透过以“我”为主角的刻画塑造,把漂浮于时代的疲乏怠倦感呈现出来。
在角田早期的作品中,很明显喜欢以片假名来处理人物的名字,往往只以第一名字或第二名字的片假名记述,流露一种存在意识稀薄,很有假设味道的气息。事实上,她早期作品中不少是以不完整的家庭为焦点,父亲的不存在更属常态。《真夏之花》中我的父亲不存在,同样在《地上八楼的海》也相若;至于在《假寐之夜的UFO》中,虽然父亲好像在故乡田野中,但处理上同样好像俨然不存。
其实不仅父亲的角色,早期的角田光代小说基本上是以淡化历史感为主要手段。所以现实上的实指尽量模糊稀释,就如《地上八楼的海》虽然以东京为舞台,甚至可推想为蒲田一带之地,但角田仍以令读者认不出确实所指的方法处理。即使处理商品也如是,在《另一窗扉》中,突然失踪的“我”之室友ASAKO是典型的牌子女郎,但小说中也淡化了现实中的品牌名字,令作品恍如一种“无印良物”式的存在。
“风俗小说”的社会性
正如絓秀实所云,《经济王宫》可看成为角田“风俗小说”的代表性作品,内里除了出现大量实指的品牌名字以及地名,更重要的是连人物的构成设定也开始出现具体的名字,而再非仅以片假名交代。在狭小房间中同居的包括没人气的作者及兼职员“我”,以及无业的YASUO,两人身边出现大量具名字的人物,如在餐厅兼职的中村勇男以及同事滨野先生等,甚至连“我”的老家为山梨县都有明确交代。
当然,在风格改变的背后,角田肯定的是由个人经验的延伸写作方向,转化为与社会背景加上紧密扣连。她的代表作之一的《树屋》,正是由底层出身的男女出发,透过他们的家族历史,记述三代人由殖民地时代的“满洲”到战后日本新宿的转移故事,登场人物及地名均有实质的具体指涉,而且当中的满铁电影、苏联参战、战后的市场、六八的学生运动,甚至到九五年的奥姆真理教事件均一一出现,对细节描述绝不马虎,正式完成向“风俗小说”的转化。
由“私小说”至“风俗小说”的演化,处理手法或许有所更易,但角田光代关心的家族命题始终如一,就以《树屋》而言,就是把由个人角度切入底层的习性,改为背靠更宏大的社会背景,而这一点对作为作家角田光代而言,也是成长的驱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