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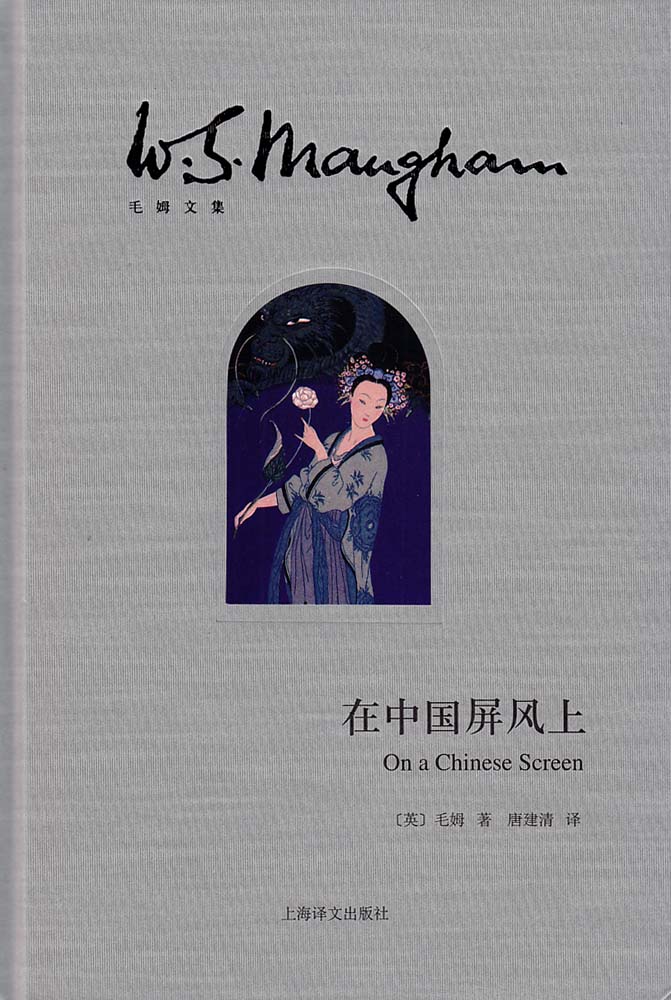 上个世纪80年代,日本人评选世界上最伟大的作家,不分古今,莫辨日外。结果第一名毫无悬念地是莎士比亚,第二名则让西方人吃了一惊:Somerset Maugham。毛姆在西方正典中没有位置,一不留神就划归到“二流作家”行列,精英们不一定喜欢他,嫌他不够沉重;普罗大众也不一定喜欢他,嫌他不够浅显;但是中间阶级的人士天然地喜欢他,喜欢他对人性的探索、对欲望的悲悯,同样是这类题材,茨威格往往写得泪如雨下,但是毛姆写来就颇为冷静,有一种英国式的冷幽默。中国人里喜欢毛姆的人也很多,最有名的当数张爱玲。熟悉毛姆的读者,读着读着张爱玲想起毛姆的,肯定不止周瘦鹃一人。不过毛姆不像张爱玲那么天才,全靠向壁虚构就可以胸有成竹。毛姆基本还属于老派的作者,除了读万卷书,尤重行万里路,在行路中认识人性的浩大、复杂和幽深,并且乐在其中。同时,毛姆也不像张爱玲那么虚无,他有自己的尺度,那是现在已经不再流行的绅士的尺度:勇气、荣誉、同情、自律、理想,在世风日下的现代社会,葆有最后的优雅和坚持。 上个世纪80年代,日本人评选世界上最伟大的作家,不分古今,莫辨日外。结果第一名毫无悬念地是莎士比亚,第二名则让西方人吃了一惊:Somerset Maugham。毛姆在西方正典中没有位置,一不留神就划归到“二流作家”行列,精英们不一定喜欢他,嫌他不够沉重;普罗大众也不一定喜欢他,嫌他不够浅显;但是中间阶级的人士天然地喜欢他,喜欢他对人性的探索、对欲望的悲悯,同样是这类题材,茨威格往往写得泪如雨下,但是毛姆写来就颇为冷静,有一种英国式的冷幽默。中国人里喜欢毛姆的人也很多,最有名的当数张爱玲。熟悉毛姆的读者,读着读着张爱玲想起毛姆的,肯定不止周瘦鹃一人。不过毛姆不像张爱玲那么天才,全靠向壁虚构就可以胸有成竹。毛姆基本还属于老派的作者,除了读万卷书,尤重行万里路,在行路中认识人性的浩大、复杂和幽深,并且乐在其中。同时,毛姆也不像张爱玲那么虚无,他有自己的尺度,那是现在已经不再流行的绅士的尺度:勇气、荣誉、同情、自律、理想,在世风日下的现代社会,葆有最后的优雅和坚持。
《在中国屏风上》(On a Chinese Screen)是毛姆1919-1920年中国之行的产物,包括58篇原本可以写成小说的“素材”,此刻连缀成一组中国之行的“叙事”。译者唐建青指出毛姆与现实中国的“隔”,用曾经流行的术语,是“想象的异邦”,这倒是有点苛求了。走马观花也好,雾里看花也好,“观看”不可能是纯然“客观”的,但是只要观看了、并且是在踏实的行走间观看了,终究是值得肯定的。时年45岁的毛姆在冬季溯长江而上,旅行了1500英里,他显然是一个热情、好奇、能吃苦的旅行者——在污秽邋遢的小客栈,一个过路文人挥毫泼墨,而在梅花与小鸟的画面中,毛姆“领悟了永恒的真谛”;在寒风刺骨的夜晚,简陋的舱房里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但是毛姆却能感觉到“罗曼司”——一种无所从来的狂喜。山光水色、雾气云影、破败的村庄、喧闹的小镇,在写景状物的字里行间,跃然而出的是毛姆本人的赤子之心。旅行者不可避免要“猎奇”,所以毛姆也未能免俗地去鸦片烟馆体验生活,但是他总体的态度不是游客式的少见多怪,更不是殖民者的指手划脚,而是持守着旁观者的距离和清醒,于是在很多时候,“旁观者清”。一路上偶遇的人们,诸如穿着体面而笨拙地牵着一头小黑猪的老人,江边有条不紊地行着祭奠之礼的老妇,朝气蓬勃带着一只鹦鹉的小伙子,饱经沧桑目光坚定的蒙古人首领,虽不过是小幅白描,毛姆却都能写得趣味盎然、气韵生动。一路行来他接触最多的中国人是苦力,所以《驼兽》和《江中号子》等篇寄予了他深刻的人道主义同情。除此以外,他认真写中国人的有三篇:《内阁部长》刻画了一个腐败贪婪的官僚,但是在面对艺术品的时候,有一种“迷人的温情”;《戏剧学者》写一位“现代比较文学教授”,虽然有留学国外的背景,但是视野狭隘到令人发噱;《哲学家》写大名鼎鼎的辜鸿铭,作者发挥了写人性的特长,将一代鸿儒的故作高傲、自我标榜、酸腐、落寞、尖刻写得跃然纸上,加上鸦片烟瘾、对花街柳巷的入迷、对小女儿的疼爱,特别是临别挥毫赠情诗的莫名其妙,可谓写活了一个特立独行的中国知识分子,而且写得严谨中正,没有强作解人之嫌。
译者分析了“在中国屏风上”这一题目,指出“屏风”有呈现、点缀、遮蔽的功能,进而说明毛姆与真正的中国的隔膜。其实,正如西方评论者所指出的,这一标题的象征功能异常丰富,里面有着多重含义。首先,屏风上的画面介于连续与不连续之间,以此概括58篇联系松散的速写,颇为精当。其次,在20世纪初期,绝大部分英国人对于中国背景的认识不过是“中国式屏风”,这样的屏风曾经充斥在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客厅中,不一定是“中国制造”,但是有着“中国趣味”,亭台楼阁、山林湖泊,有“东方装扮”的小人徜徉其间,Chinese Screen是“异国情调”的代名词,反映的是英国人的中国想象。英国人与中国人隔着无形的屏风,声气相闻而又自行其是,形成反差极大的两个世界,特别是英国人的老大心态,使这种屏风根深蒂固、难以逾越。对这种一屏障目不见泰山的现象,毛姆是颇有微词的,他希望向英国读者提供他所看到的中国的一幅真实而生动的画面,所谓的“在中国屏风上”更多的是反讽的手法。第三,毛姆的具体操作办法是“在中国屏风上”添加英国人形象,这也是本书最成功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