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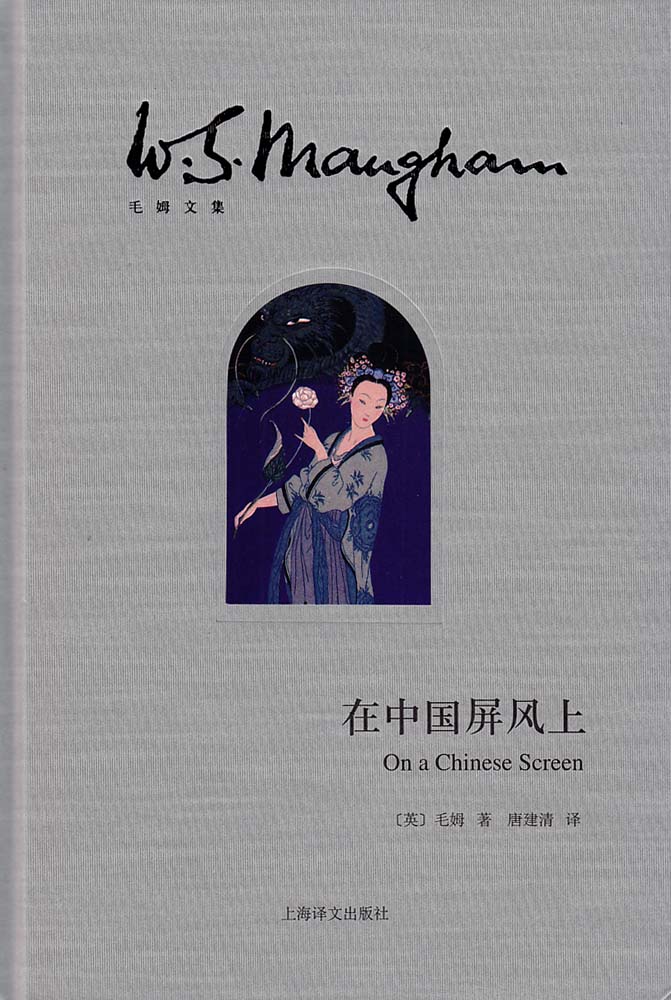 毛姆的《在中国屏风上》算不得是深刻的中国观察毕竟他于1919年至1920年顺长江溯游而上的游历只有几个月的光景。对于如此幅员辽阔的国家,恐怕没有任何人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形成如何深邃的认知。毛姆很知趣熨帖地将自己的这个系列游历文章命名为“在中国屏风上”,意味着他知晓自己的“他者”眼光,以及不可避免的书写平面化。而他肯记录这五十几则短章,则表明对游历的这片异域土地的兴趣与关注,以及一种善意的姿态。 毛姆的《在中国屏风上》算不得是深刻的中国观察毕竟他于1919年至1920年顺长江溯游而上的游历只有几个月的光景。对于如此幅员辽阔的国家,恐怕没有任何人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形成如何深邃的认知。毛姆很知趣熨帖地将自己的这个系列游历文章命名为“在中国屏风上”,意味着他知晓自己的“他者”眼光,以及不可避免的书写平面化。而他肯记录这五十几则短章,则表明对游历的这片异域土地的兴趣与关注,以及一种善意的姿态。
对现时的中国读者而言,读一位名作家对近百年前中国的素描式书写,既是借助他者的视域看那一段历史中的中国,更可体味这一扇中国屏风为何会呈现如此的形态。
毛姆是小说家,但《在中国屏风上》却是一组速写“一组中国之行的叙事”,“我从中发现了一种新鲜感,那些文字是在我记忆鲜活的时候记下来的,而如果我将它们精心加工成一个故事,这种感觉就会不复存在”。毛姆忠实于自己的感觉,亦说明他对自己作家身份的尊重,他不是一个肤浅懵懂的游客,也不是趾高气扬的殖, 民者,而是好奇的、富同情心的观察者。他的眼中与笔下不仅有“巨大、雄伟、令人敬畏的中国长城”,奔流不息的长江,变化多端的山川景物,更有辛苦劳作的苦力,宁静的鸦片烟馆,凋敝破败的山城,以及通晓中西却扎着根细长辫子的中国学者,有良好的鉴赏力同时贪污巨万的内阁官员,研究比较文学、视野却颇为狭窄的大学教授。
毛姆眼中的中国与想象中的中国并行不悖,奇异的共存共生。如在街市上,“一匹毛色光洁的骡子,拉着一辆北京来的轿车缓缓而行”。这对本地人看来无甚新鲜,但在毛姆的遐想中,车中坐的或许是一位饱学之士去拜访友人,“共同追忆那一去不返的唐宋盛世”,或许是一位歌女去赴宴,“与那些风流倜傥的公子哥们雅致地酬, 答”,“北京轿车似乎载着所有东方的神秘,消失在渐浓的夜色中”。
如此的中国形象显然并非仅仅是毛姆一时一地所见可构筑,而是西方在过往的几个世纪中对中国的文化想象在毛姆这里的微妙折射。神秘、异域风情、有着辉煌文明等标签,不可避免地影响着毛姆观望中国的眼光,在寻常的事物之上加诸遥远的文化传统的印记。
但毛姆所游历的上世纪初之中国现实的凋敝与残酷,不可能为一个忠实的记录者所忽略。毛姆沿江而上,看到拉船的纤夫在举步维艰中发出号子,“这声音几乎不是人发出的,那是灵魂在无边苦海中有节奏的呼号,它的最后一个音符是人性最沉痛的啜泣”。
有着人道主义关怀的毛姆记录下了所闻所见,大约那个想象中的神秘古国与眼前的残酷碎片错织,使其内心充满了迷惑,由此生出另一种误读。如他参观鸦片烟馆,认为“这地方真令人愉快,像家里一样,舒适而温馨。它令我想起柏林那些我最喜欢的小酒馆,每天晚上,劳累了一天的人们常在那里享受安逸的时光”;看到一个矮胖的官员和苦力们聊天,认为东方更具有平等观念,“我敢说,也许臭水沟比议会制度更有利于民主”。这是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想象中的错位,停留于表象,无法深入肌理,有了不乏滑稽的效果。但我们也可体会出,毛姆的书写尽管时有谬误,但仍是善意的,虽算不上到位,却是尽力的同情之理解,并映射出他对这个东方古国残留文明教化的小心翼翼的捕捉。
毛姆于书中亦将相当的篇幅给了在华的英国同胞们,且并未吝惜讽刺笔墨,活生生勾勒出种种嘴脸来。如骄傲于在中国生活5年却一句中国话不会说的商行大班,自信自己屋子里没有一件中国货的洋行老板,声称关怀劳苦大众的大人物毫无犹豫地猛踢车夫的屁股,愤怒于英国女人嫁给黄种人的领事,靠妻子出轨收取岳父补偿金致富的精明商人等等。可以说,这是“中国屏风”的另一面,与中国的风土故事相得益彰,共同构成在他者的视域中,叙事如何生成,及与自我的镜像如何相互补充,以获得生活的全貌。
毛姆的中国叙事已过去近百年,不管是那段遥远的岁月,抑或来自域外的讲述,于我们而言,似是双重的陌生。然而陌生未尝不能带来有益的新奇,审视自己的历史,关照他人的眼光,或许能够获得新的视角,以及新的认知。毕竟,即使是平面化的时世掠影,亦包涵有丰袤的文化意味,供多元的解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