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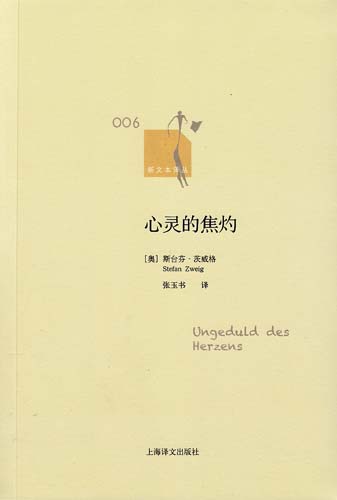 在唯一的长篇《心灵的焦灼》中,茨威格的叙述看来并不高明。引言——摘自康多尔大夫说的一段话:同情恰好有两种,一种同情怯懦感伤,实际上只是心灵的焦灼,即把小说的主旨和盘托出。一切不出所料,后面的故事就围绕这个主题不紧不慢地展开:奥匈帝国骑兵少尉霍夫米勒偶然结识下肢瘫痪的少女艾迪特,出于同情常去陪伴,天长日久,艾迪特对他萌生了爱情。经过一番痛苦的内心挣扎,霍夫米勒答应与她订婚,但旋即后悔。艾迪特得知霍夫米勒毁约,痛不欲生,跳楼自杀。霍夫米勒因此带着沉重的负罪感而抱恨终身。 在唯一的长篇《心灵的焦灼》中,茨威格的叙述看来并不高明。引言——摘自康多尔大夫说的一段话:同情恰好有两种,一种同情怯懦感伤,实际上只是心灵的焦灼,即把小说的主旨和盘托出。一切不出所料,后面的故事就围绕这个主题不紧不慢地展开:奥匈帝国骑兵少尉霍夫米勒偶然结识下肢瘫痪的少女艾迪特,出于同情常去陪伴,天长日久,艾迪特对他萌生了爱情。经过一番痛苦的内心挣扎,霍夫米勒答应与她订婚,但旋即后悔。艾迪特得知霍夫米勒毁约,痛不欲生,跳楼自杀。霍夫米勒因此带着沉重的负罪感而抱恨终身。
茨威格以第一人称“我”切入叙述,转而切换到霍夫米勒的第一人称视角中,让我们不知不觉融入他跌宕起伏的心灵世界。艾迪特的自杀也把我们引入了一个道德选择的困境:这是谁之过,霍夫米勒是否需要为此负罪终身?这一质问为“爱与同情”的命题做了最好的注解。然而我们不禁感到疑惑:除了开头部分,“我”这个后来再也没有出场的人物承担了一小部分叙述功能,通篇小说近乎是霍夫米勒的现身说法,霍夫米勒的故事如何撑起了这部30多万字的小说?
作为在小说叙述上力求简洁明快的作家,茨威格绝不容许自己的作品冗长繁琐,小说鲜明的主题却让一些“旁逸”的枝节轻轻滑过了我们的视线。实际上,小说讲了三个“爱与同情”的故事。康多尔大夫是霍夫米勒整个心路历程的见证者,他在行医过程中认识了瞎女人克拉拉,放弃优厚的条件与她结婚,在给她带去幸福的同时,他也获得了心灵的宁静。他以积极的行动为“爱与同情”树立了范本,正是他一次次洞悉了霍夫米勒的懦弱,在关键时刻促使他承担起责任。
也正是这个长期为艾迪特做诊疗的康多尔大夫,让我们知道了艾迪特父亲开克斯法尔伐的故事。这个本名叫卡尼兹的犹太人,原先穷困潦倒,一次偶然的机会,他介入开克斯法尔伐庄园遗产事件,费尽心机骗取庄园新继承人狄称荷夫的信任,顺理成章地当上了庄园的主人。出于未泯的良心,他娶了狄称荷夫,与她生下了女儿艾迪特。命运却没有因为他的“赎罪”而善待他,先是妻子早逝,继而他把所有的心思寄托在女儿身上。悖谬的是,正是他的倾心关爱和霍夫米勒的“同情”促成了艾迪特最后的自杀。
三个“爱与同情”的故事相互关联又各自独立,支撑起了整部小说的构架。而这三个人物之间紧张微妙的关系,使叙述充满了张力。挂在茨威格的琴弦上,我们听到的不是霍夫米勒一个人的内心独白,更像是一出“爱与同情”的三重奏。
小说写于1938年,距茨威格夫妇在巴西自杀仅四年。茨威格一生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深切感受到霍夫米勒式同情带来的严重后果。他深知怯懦地追随战争,默默承受苦难,并不是一种负责任的选择,只有选择担当和抗争,才有可能真正远离心灵的焦灼。由此,小说实际上呈现了茨威格一个人的“战斗”。然而茨威格让霍夫米勒为错误的“爱与同情”承担了一生的负罪,作为创作者,他却以服毒自杀的方式,匆匆挣断了生命的琴弦,那戛然而止的一声断裂摧人心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