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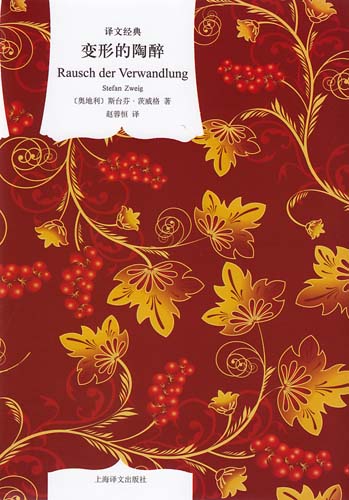 长篇小说《变形的陶醉》出自奥地利著名作家茨威格的笔下。与他的《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等名作相同,茨威格依然将一个结构并不复杂的故事,讲述得让人无法释卷,而究其原因,得自于茨威格细节描摹的娴熟。 长篇小说《变形的陶醉》出自奥地利著名作家茨威格的笔下。与他的《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等名作相同,茨威格依然将一个结构并不复杂的故事,讲述得让人无法释卷,而究其原因,得自于茨威格细节描摹的娴熟。
《变形的陶醉》主人公仍然是女性——二十八岁的克丽丝蒂娜。这奥地利姑娘的哥哥丧命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场。因托人说情,她才在克莱因赖芙林小镇的邮务所获得个助理职位,她依靠菲薄的薪金,与贫病交困的寡母拮据度日。这天,一份突如其来的电报,闯入她那麻木苍白的生活,让她多年来独自一人在邮务所工作的机械节奏,有了一个暂停的间隙。茨威格在小说开端,先不嫌琐碎地用细节堆积出乡村小镇邮务所环境的陈旧,数落着邮政所用具的杂乱。翻阅小说的人们正是通过如此琐碎的细节,逐渐进入乡村小镇的场景。它们平庸、乏味,散发着奥地利战后所遗留创伤的陈腐气息,吞噬着克丽丝蒂娜残存的、已经少得可怜的青春年华。居住在美国的姨妈姨夫来瑞士旅游胜地休假,邀请外甥女克丽丝蒂娜来瑞士相聚。这份电报给了她一个机遇,她终于可以摆脱多年来乡村小镇那死气沉沉的生活了,纵然是暂时的。小说家茨威格所擅长的,就是描绘女性的情感波澜,特别是在其面临身心境遇变化大起大落的时刻。《变形的陶醉》中,他描摹克丽丝蒂娜从奥地利小镇进入瑞士的途中,被压抑多年的感觉之萌动、复苏。当然,他着重刻画的是这个二十八岁的姑娘之心境变幻:收到电报的意外惊喜,准备行装的囊中羞涩,进入豪华宾馆的自惭形秽,初试华美衣衫的手足无措,瞬间居然成为高贵社交场合聚焦美人的欣喜万分,沉湎于灯红酒绿应酬中的天真放纵,被名利场嫉妒目光识破真实身份的百般尴尬,收拾寒碜衣装只身走出豪华宾馆的无奈落寞……叙述克丽丝蒂娜从灰姑娘到公主,又回复灰姑娘的原本身份这一情节,茨威格笔触所调遣的,依然是大量细节组成的心理描写:豪华宾馆的陈设,富丽衣裳的色泽,体肤被美丽衣饰抚摸、包裹、簇拥的细腻触感,美貌被羡慕目光注视、赞赏、追逐的心醉神迷,阴差阳错的误会使村姑被抬升成贵族小姐的晕眩,情窦初开的心灵遭遇英俊富裕男性情感诱惑的颤动……正是如此众多细节的铺垫,将克丽丝蒂娜的变形和陶醉———她人生中一个华彩乐章,即便是一次暂时的错位,演奏得如痴似醉。同时,因为喜极而悲的急剧变化,使随之而来的她人生的复位,显得尤其残酷。其实,茨威格在《变形的陶醉》中设置的情节,就是要展现克丽丝蒂娜的人生变奏。按照文艺美学的理论,用善恶对立之极端的对比和强烈的情感诉求,表现世俗社会中的各种矛盾,将刻骨铭心、富有艺术感染力的表演和道德解释框架进行组合,是一种美学模式。它使观赏者相信,世间万物在道德层面是可以被清晰读解的。而人们读解时依仗的,也是这种美学模式试图通过表述唤醒的,是一种与人类的潜意识相似的“神秘道德感知”。它储藏着传统神话的碎片和残余物,属于精神价值的领域。但是艺术功力深厚的小说家,蔑视用非此即彼的善恶对立,讲童话色彩的道德故事。他们着力描摹的是人世间善恶对立的变形,和各种社会角色在欲望诱惑中的沉浮,人性的复杂才是他们愿意孜孜不倦探索的。
《变形的陶醉》中展现克丽丝蒂娜的人生变奏曲,固然是从她离开乡村小镇去瑞士之行开始的,但她沉湎于名利场的欢乐,陶醉在错位的变形中的种种描写,纵然是浓墨重彩,或许并非是全书的高潮。因为据中译本之译者介绍,这个小说的文本,只是茨威格写于20世纪30年代初,原名为《邮务小姐的故事》的初稿。写出后他无暇修改。1982年由克努特·贝克整理,从此书稿中抽取“变形的陶醉”之文字作为书名出版。书稿原作中,那个在小说后半部才出场的费迪南先生,形象与克丽丝蒂娜相比,大为逊色,甚至可以说个是用书面文辞堆积、并非细节生动描摹的干瘪角色。他怂恿克丽丝蒂娜盗窃邮政钱款,共同亡命天涯的行为,可谓是她人生变奏曲之强烈变异。倘若茨威格有暇修改《邮务小姐的故事》初稿,那么作家很可能会用细节描摹,为费迪南先生注入血肉,使他除了怨恨的愤怒唠叨,还有更多施展身手的机会。不然的话,克丽丝蒂娜与费迪南成为一对“雌雄大盗”的故事结局,有可能会索然无味,既败坏了读者的胃口,亦有负于作家的英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