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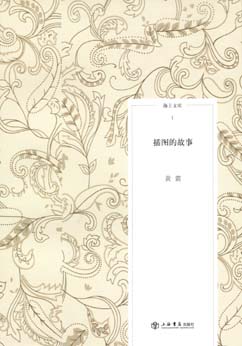 得悉黄裳逝世是读了陈子善的微博:“我极其沉痛地向微博的朋友们报告,著名散文家、藏书家黄裳先生刚刚离开我们,享年九十三岁。”他还说:“黄裳老先生因年事已高,今年6月,曾因感冒引起肺部感染在瑞金医院住了一个月,出院后越来越衰弱。之后又住了一次医院,但只住了一晚上就吵着回家。前天又觉得不舒服,被送进医院。5日早上我还和他女儿通过电话,没想到傍晚就走了。” 得悉黄裳逝世是读了陈子善的微博:“我极其沉痛地向微博的朋友们报告,著名散文家、藏书家黄裳先生刚刚离开我们,享年九十三岁。”他还说:“黄裳老先生因年事已高,今年6月,曾因感冒引起肺部感染在瑞金医院住了一个月,出院后越来越衰弱。之后又住了一次医院,但只住了一晚上就吵着回家。前天又觉得不舒服,被送进医院。5日早上我还和他女儿通过电话,没想到傍晚就走了。”
读了这话,我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莫名的惋惜,更觉突兀的茫然与哀伤。特别是那句“只住了一晚就吵着回家”!是的,我想,数十年长期徜徉在小书屋中的黄老,怎住得惯那人流如海、熙攘不息的医院呢?他多么留恋那“榆下说书”的老屋,这书屋虽小,却是他生命的全部。而况他还有许多东西要写,有许多事要做,许多话要说……所以,当噩耗传来,我不禁心里一怔,因为几月前,我还收到他老的信及签赠之书,但怕打扰他,复信迟迟,可如今一切晚了,我还能做什么呢!
今晚,正是“风飘白露天,月色又朦胧”之际,我与黄老神交面交的回忆闸门,乃慢慢打开。记得第一次到他家拜访,是在丙戌冬至前二日,因与复旦大学联合举办“皕宋楼藏书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特去沪上,来去匆匆,所余时间不多,但同行三人,均想去拜访著名学人与藏书家黄裳先生。为方便起见,我们就入住离黄老家很近的城市酒店。那晚约好第二天上午十点到他家。翌日,早餐后,我们步行至陕西南路、靠近复兴路口的陕南邨,附近有一个加油站,等了一会,待复旦陈麦青先生赶到,便一起前往。
这陕南邨内,百年法式老洋房,一栋栋林立在那里,环绕四周,翠绿的梧桐衬着淡黄色墙体,间有香樟、榆树、芭蕉、紫藤,望去煞是优美。相比隔墙之外,是熙攘的市嚣,恍有隔世之感。我们拐了两个小弯,走进这153号的老洋房,拾级而上,楼梯陡长,层层环形,当走至三楼一个黑色铁门口,就到黄裳家了。
因早通好电话,当我们把门鈴一钦,黄老马上自己来开门了。他拖着慢悠悠的步子,把我们迎入客厅。客厅不大,一张黄旧的长沙发,前一矮矮的茶椅,左右配上两小沙发,靠北墙和东面分别有两只旧书橱,墙上各挂字画。一幅是他老友黄永玉的荷花,另一幅若没走眼,应是明代沈周的作品。这天,因我们是一行五人,他女儿容仪忙从别的房间拿了几把椅子来。
进屋甫坐,见黄老身体尚好,个子不高而胖胖的,有些耳背,见此状,近他身旁坐着,如此,我只需稍稍左侧,就能方便与他面对面交流起来。说起今年五月,我们几位有机会去日本东京静嘉堂阅读宋版书的事,想听听黄老对被视为国宝的宋版书的看法。我说:“我们此次拜访,想请黄老给我们指教有关皕宋楼藏书的学术会议。”当听到我们就皕宋楼和静嘉堂的藏书向他请教,刚才还是呆板着、无多大表情的他,也就兴奋起来,他带着很浓的地方口音、似有点沙哑的嗓音即发话了:“国内宋版书越来越少,我曾说过,湖州陆心源的宋版书,1907年悉数给静嘉堂收藏去了呢。我看过一些宋版书,但我之收藏大多是清代,已出的《清代版刻一隅》可窥其一斑。以往人们关注版刻图书,大抵以宋元刻本为主,明刻就少了,清刻更寥寥而已。”就此话题,黄老与我们似很快拉近了距离,大家谈兴也更浓了起来。
正谈不多时,突然黄老独自站起来,悠悠然地一个人走到隔壁房间里去,不一刻,他就拿出了一部清刻本,取掉夹板,兴致很高地说道:“我最近买到了一部好书,你们看,就这一册,并不厚,但价不菲,你们看看这部书多少价?”一听这话,大家只能闭口哑然,因我们中除麦青先生懂版刻外,谁能鉴定这部清刻本之现价呢?此刻,突想起李辉对黄裳的描述:“黄裳颇不善言谈,与之面对,常常是你谈他听,不然,就是久久沉默,真正可称为‘枯坐’。电话更是简洁得要命,一问一答,你问几句,他答几个字,绝无多的发挥。”
然而,现在我左侧坐着的黄老,似乎没有像李辉说的那么俨然,这次大家就藏书、版刻的话题谈开了,无一点默然状。瞬时麦青拉高了点声音,对黄裳说:“这次特带来一部陆心源的《仪顾堂集》,是光绪年间刻本。你看看版子如何?”此话一落,我们打开了八册一函线装本放在他面前,黄老一本本慢慢地翻阅,此刻,屋子所有的人倒真“呆坐”等他了,无一点声响。我瞧着黄裳红润润的脸色,他穿的黑色皮夹克外套,在他家南窗阳光映射下,一闪一闪地泛着光亮,连他短短的白发、带些红斑的一圈圈发根处,也闪烁发亮。原本垂下的眉毛,因他正在阅书,似更下垂了。黄老虽年近九十,且正值严冬,看上去挺精神、记忆力非常好。见此情状,我想起了他的《榆下说书》一书,他家楼后那棵榆树,此刻是否也会闪发出红红的笑颜……但是,紧接着我就听到他粗嘎的发音,突然把我的浮想全打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