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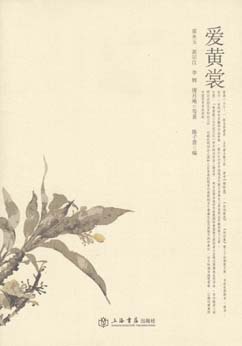 黄裳生于1919年农历6月15日(公历7月12日),祖籍山东,原名容鼎昌,是满洲镶红旗人。中学在南开中学就读,与红学家周汝昌、剧作家黄宗江是同学。黄裳算得上是中国读书界的传奇人物,他于1940年考入交通大学电机系,而投考交大电机还是因为他父亲的缘故,“因为父亲的主张,要我投考有名的交通大学,好完成他实业救国的宿愿。”“5道数学题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证出一道,而且还不是正规的解法”,黄裳自认为考得并不好,但国文和英文都很优异,结果还是被录取了。“后来知道这是交大主持人唐蔚芝老先生的主张。特别重视的是国文考分,数理方面却在其次。” 黄裳生于1919年农历6月15日(公历7月12日),祖籍山东,原名容鼎昌,是满洲镶红旗人。中学在南开中学就读,与红学家周汝昌、剧作家黄宗江是同学。黄裳算得上是中国读书界的传奇人物,他于1940年考入交通大学电机系,而投考交大电机还是因为他父亲的缘故,“因为父亲的主张,要我投考有名的交通大学,好完成他实业救国的宿愿。”“5道数学题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证出一道,而且还不是正规的解法”,黄裳自认为考得并不好,但国文和英文都很优异,结果还是被录取了。“后来知道这是交大主持人唐蔚芝老先生的主张。特别重视的是国文考分,数理方面却在其次。”
不过黄裳并未毕业,只拿到一张结业证书。他很多文章发表之后,很多人误以为他是学文出身,读的是外文系。比如历史学家吴晗在给《旧戏新谈》作序时就曾说过:“想象中此公应该是读书人家的子弟,在大学里读外语系,年纪20多岁……同时又从报纸上作者另一篇文章,知道作者不但不是外语系出来的,甚至不是文学院,是学工程的。”对于这样的误会,黄裳也曾说,“连我自己也料想不到后来的生活道路。”
在自我定位时,黄裳说自己说不上有什么专长。而他在别人眼里是什么形象呢?曾任人民日报出版社社长的姜德明说:“他本来可以成为一个戏剧家……他也可能成为翻译家……他没有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却选择了新闻工作。”钱锺书赞叹黄裳文笔极佳:“每于刊物中睹大作,病眼为明。”作家唐称誉黄裳“实在是一个文体家”。
黄裳之名的得来缘由有两说,一是艳说与黄宗英有关,说他当时是有“甜姐儿”之称的女明星黄宗英的忠实“粉丝”,有天忽发奇想,以“黄的衣裳”之义取了“黄裳”这个笔名,钱锺书后来曾为他写过一联“遍求善本痴婆子,难得佳人甜姐儿”,不知说的是不是这个典故?另一说是容鼎昌的中学同学、黄宗英的哥哥黄宗江自述,说是当年他爱戏,容鼎昌遂跟他说唱戏得有个艺名,于是便自作主张地帮他起名“黄裳”,可黄宗江觉得这个名字太过华丽,觉得还是自己父亲给的名字好,没用,没想到,后来这名字倒成了容鼎昌的笔名,且一直叫到恂然老者。对这些说法,黄裳都一笑置之,似乎未见肯定,亦未见否定。
1942年,黄裳从上海转至重庆交大,这时的他“每天在烟雨迷离的长江边上,在有着美丽名字凤凰楼的茶馆里,读读书,写写信,心里充满了少年人的离愁别绪,家国之感。”两年后,黄裳收到征调令,跟着美国兵走遍中国西南名城,从昆明、桂林、贵阳,最后到了印度。抗战胜利后,黄裳解甲归田回到重庆,在那里写下了一本随军采访《关于美国兵》。黄裳没有学过新闻学,也没有一个记者朋友,但就此走上了记者生涯,去当时重庆的中共办事处做过采访,以特派员身份采访过梁漱溟、傅斯年、周作人。1945年至1956年就任上海《文汇报》记者、编辑、编委等职。晚年,黄裳以散文大家与首屈一指的藏书家名闻海内外。
画家黄永玉眼中的黄裳几乎无所不能:“黄裳那时候的经济收入:文汇报编副刊、中兴轮船高级干部、写文章、给一个考大学的青年补习数学、翻译威尔斯的《莫洛博士岛》、出几本散文集,还有什么收入?伺候年老的妈妈,住房及水电杂费,收集古籍图书,好的纸、笔、墨、砚和印泥……还有类乎我和曾祺的经常的食客们……他都负担得那么从容和潇洒。黄到底有多少本事?记得50多年前他开过美军吉普车,我已经羡慕得呼为尊神了,没想到他还是坦克教练!……”
巴金是影响黄裳最深的朋友,对于巴老,黄裳曾回忆说,“我就不记得他对我讲过什么理论,文学上的事情也讲得很简单、很少。我照例得到文化生活出版社新印成的每一本书,包括他自己的译作。看到一本新书印成,是真正使人高兴的事情。当时我在报社里当记者,每天要写许多各种样式的文字,他也从来没有对我说过什么意见。后来报纸被封门,我也失了业。他就把这些文章要去,选了一下,印成了一本小书;又建议我翻译冈查洛夫和屠格涅夫的小说,(巴金)夫人的译本也是他借给我的。我偶然走上文学道路,就是这样开始的。对这样一位在前面引路的前辈的帮助,我一直怀着感激的心情。当时人们生活、工作的方向都很明确,对那个旧社会、旧制度,大家早已取得了一致的意见,用不着进行什么多余的议论了。只要努力工作,在不同的岗位上,使用不同的武器,用不同方式努力加速它的灭亡就是。巴金在二十年中写下的十四卷文集就是这种一贯努力的证据。”在巴老过世之后,黄裳写下《伤逝》一文,上海巴金纪念馆馆长周立民曾说,这篇《伤逝》是纪念巴老最好的文章。
黄裳活到老写到老,在散文、戏剧、新闻、藏书等领域均有建树,与梅兰芳、巴金、郑振铎等文化名人相交甚笃。著有《锦帆集》、《妆台杂记》、《过去的足迹》、《珠还记幸》、《金陵五记》、《银鱼集》、《榆下说书》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