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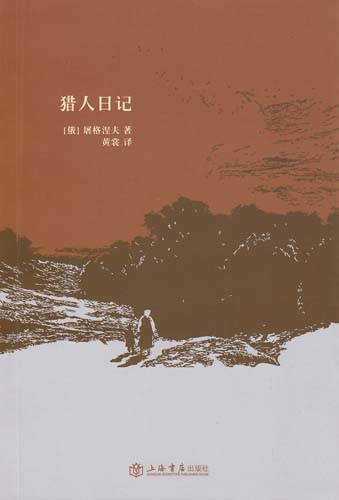 黄裳与文学山房第三代传人(现在的“文育山房”主人)江澄波曾有过交往。江澄波先生退休前长期在苏州古旧书店工作,黄裳因访书或其他事情多次来苏州。新中国成立前,护龙街一带有许多旧书店。后来,经过公私合营等多次商业改造,苏州专业经营旧书的只剩一家古旧书店。所以,每次到苏州,黄裳都要到书店来,买了不少书,并且还留下了不少与苏州有关的文字。 黄裳与文学山房第三代传人(现在的“文育山房”主人)江澄波曾有过交往。江澄波先生退休前长期在苏州古旧书店工作,黄裳因访书或其他事情多次来苏州。新中国成立前,护龙街一带有许多旧书店。后来,经过公私合营等多次商业改造,苏州专业经营旧书的只剩一家古旧书店。所以,每次到苏州,黄裳都要到书店来,买了不少书,并且还留下了不少与苏州有关的文字。
黄裳是苏州女婿,他的夫人家住桃花坞。因此,他对苏州有一种特别的情感。1984年2月,他写了一篇《我看苏州》,文中写道:“虽然不是苏州人,但对我来说,苏州实在是有如第二故乡那样的地方。”上世纪四十年代起,黄裳总是隔一两个月就要来一次或几次苏州,几十年来曾来过多少次苏州,他自己也记不清了。
黄裳认为,苏州不只是旅游城市,她是一座文化古城,“她的一切特点,都和两千多年来的文化积累分不开。”他说,苏州的山水并不雄奇,只是因为曾经有许多著名的人物来过、看过、居住过,才变成了名胜与古迹。
1978年深秋的一天,黄裳一个人跑到南门汽车站,登上了去洞庭杨湾的公共汽车。他独自上山游览,尽情观赏漫山遍野的栗子、银杏、枇杷等,各种植物,走进了隐蔽在浓绿中的古庙,庙里有个小小的庭院。黄裳坐在白云居里一边喝着本山供应的碧螺春,一边赏着小院里古老的山茶、短垣和墙外的满山苍翠。这座古庙就是有名的紫金庵。
黄裳对苏州美食是情有独钟的,他在朱鸿兴吃过葱油开洋面和虾爆鳝面,在王四酒家吃过午饭,那副翁同龢写的“带经锄绿野,留露酿黄花”的对联挂在柱间,是他晚年的最佳制作,“有一种颓放的腴美,好像一个吃醉了的胖老头儿。”
除了饮食、园林以外,黄裳一再表示,苏州对他的最大吸引力是书。这方面的文章写了很多,如《访书》、《姑苏访书记》、《苏州的书市》、《我看苏州》等等。《苏州的书市》一文中,他对苏州的旧书店非常怀念:“虎丘、山塘街、灵岩、天平、拙政园、松鹤楼、元大昌……这些当然都是使人流连而不忍去的所在,不过说到底,苏州对我最有吸引力的是那些旧书铺、书摊。”
1948年秋天,正是鲃肺汤上市的时候,黄裳陪叶圣陶、郑振铎、吴晗到苏州旅游。那天晚上,三个人在酒楼上喝酒,喝得几乎快要酩酊大醉了。吃罢夜饭,已是七八点钟了,郑振铎忽发豪兴,要去访书。书店早已关门,他们一家家敲开了门进去看。在玄妙观的一家书店里,主人拿出三本书来,其中一册是嘉靖赵府味经堂刻的《谈野翁试验小方》,板式很特别,巾箱本,板框四周是阴文刻花的阑。郑振铎撺掇黄裳买了下来。同时,黄裳还买了一本康熙刻的《骆临海集》,价格很便宜,随手就送给了吴晗,因为骆宾王是他的同乡。
江南解放时,他采访回上海经过苏州,已是傍晚时分,下着潇潇暮雨,“还是捺不住下了车赶到护龙街上”。集宝斋里刚收进一批旧书,地板上堆起了一人多高的“书山”。黄裳随手抽出了一本清初刻的女词人徐灿的《拙政园诗余》,高兴极了。黄裳显得有些激动,“此书的同乡、著名藏书家吴兔床也不曾见过……像这样以极偶然得的机缘得到善本的事,在别的地方是难得遇到的”。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黄裳还经常到苏州来,有时会住上两天。店里的店员(包括江澄波)每次都要请他到楼上去坐一下,他也总是要求他们拿几种书出来看看。他曾在书店里得到过一本乾隆原刻的《冬心先生画竹题记》,虽然不过十来戊,但用的是旧纸。黄裳说:“我不敢断定这是宋纸,但和宋代印刷佛经的用纸是相近的。”
除了这些访书的文章,还有很多文字与苏州有关,《吴门读曲记》、《访叶圣陶翁》、《花步》、《文征明及其他》等等,基本上都收录在《小楼春雨》(忆江南丛书,王稼句主编)一书中。1955年,黄裳和盖叫天一起游邓尉山,在禅房喝了一杯极淡的本山茶后,坐原车回去。他坐在车上,欣赏着窗外的景色:“从一望无际的碧绿的桑田仿佛可以看到苏州有名的织锦,美丽得像天上的云彩似的云锦。在春天的傍晚,邓尉附近的山光水色里,也正美丽如画。好一片锦绣的山河!”
黄裳沉浸在美丽的苏州山水中,仿佛醉了。
(张建林,苏州吴江诗人)
爱黄裳 最好莫过读其书◎李佳怿
黄裳先生于9月5日傍晚辞世,享年九十三岁。先生一生痴书,而爱书人也痴爱着先生。怀念先生,最好莫过读其书。
先生辞世前一个月,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其著作《纸上蹁跹》、译作《猎人日记》,皆为其早年作品的再版,谨此表达对先生的敬意和尊爱。不想竟成为先生生前最后出版的两书,所幸先生均及见之。
《纸上蹁跹》是先生关于中国京剧故事的一部作品,1985年译成英文由新世界出版社出版。2006年,美国Better LinkPress重版此书。此次,黄裳先生将此书稿重新整理,改名《纸上蹁跹》,交由上海书店出版社作为“海上文库”之一出版。此书收录作者用写意笔法写就京剧片段的妙文十余篇,既是对儿时剧场回忆的优美再现,更是老人童心常在的珍贵记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