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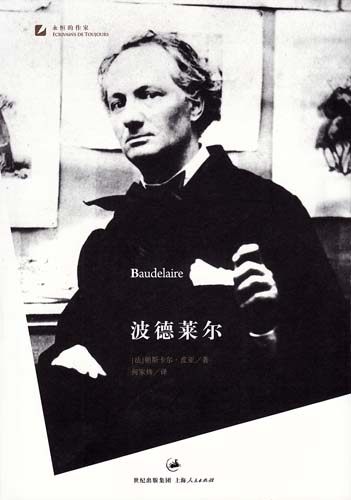 此书是诗人波德莱尔的评传,与厚比砖头的传记相比,评传要亲切得多。它轻松俏皮,读来流畅,像一个美艳而热情的姑娘,丝毫没有拒人千里的意思。就算不懂《恶之花》,也不妨碍你读这本可爱的书,并通过它去了解波德莱尔这个“五毒俱全”的极品男人。关于他,江湖人送绰号波哥,传奇故事可谓多矣。 此书是诗人波德莱尔的评传,与厚比砖头的传记相比,评传要亲切得多。它轻松俏皮,读来流畅,像一个美艳而热情的姑娘,丝毫没有拒人千里的意思。就算不懂《恶之花》,也不妨碍你读这本可爱的书,并通过它去了解波德莱尔这个“五毒俱全”的极品男人。关于他,江湖人送绰号波哥,传奇故事可谓多矣。
一、作为生活家的波德莱尔
波哥是一个敏感的天才。这点毋庸置疑,作为诗人,波哥的地位无须多言。但除去诗才,他的敏感和热切也是出了名的。这个经历六岁丧父、母亲改嫁的诗人,天生敏感,心带忧伤,忧郁成疾,内心深处滋养着绝望,一副骨灰级文艺青年的模样。对母亲的轻易改嫁,波哥耿耿于怀,认为母亲忽略了他,分散了对他的爱情,为此母子关系紧张了若干年。直到母亲再次成为寡妇后,二人关系才慢慢缓和。在波哥写给母亲的信里,充满了灼热的词句,不乏“你对我来说则是唯一,你是我的偶像,也是我的同伴”这样深情的句子。
虽敏感内向,但波哥可不是一个甘于寂寞的人。他对于名望有着强烈的渴求,并善于寻找机会制造话题。用今天的话说,波哥算得上是一个善炒作之人。他曾公开宣称,艺术家的创作如果不能引起任何惊奇,就是一些毫无价值的东西。如此故作惊人语,自然是为了引起关注,他就为《恶之花》中带有的神秘色彩和具有轰动效应的标题而自鸣得意。因此当《恶之花》遭受非议时,波哥情绪相当激动,申辩说人们这是否认我的一切,否认我的创造精神,甚至否认我对法语的把握,我嘲笑这些蠢货,并自信满满地说,这本书将与雨果甚至拜伦的最好的诗篇并驾齐驱。事实上,波哥的自信不是空穴来风,今日谈起文学上的现代性,波德莱尔绝对不可绕过。
一个不甘于寂寞的人,多半还是一个折腾者。波哥不但诗才满腹,还是一个时尚达人和美食家。父亲过世后,留给波德莱尔十万法郎。年纪轻轻就有这么一大笔钱,自然挥霍无度。自然引来众多注目,包括姑娘们火辣辣的目光。这让母亲非常担心,为此不断延迟交付监护账户的期限。含着金汤勺出生的波哥,偏对生活有着极为奢侈的要求,衣服要按其要求定制。别人穿宽松的裤子,他偏要选择穿紧身裤。连他喜欢的书,他付钱请最好的装帧师用皮革进行重新包装。对于吃,更是极为讲究,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对食物、糕点、和调味品都如数家珍,甚至连如何分辨淡啤酒和面包的好坏,都有一套成熟的经验,向朋友热情介绍时,文采斐然,夸夸其谈,活脱脱一个美食家,一个享乐主义者。
二、作为情种的波德莱尔
除了写诗和吃喝之外,找女人自然是必不可少的内容。公子本多情,这个多情的浪荡子自然也喜欢女人,也算是继承了法国文化传统,并发扬光大。波哥自曝是一个早熟的浪荡子,对女人充满渴望,一个女人的声音足以使他着魔,一根女人的头发也足以使他沉醉。波哥甚至认为,真正的艺术家就应该如此。
波德莱尔把大把时间花在美术馆、图书馆,以及艺术家朋友还有姑娘们身上。姑娘们自然愿意与这个有钱的年轻诗人进行交往,甚至轻易地就会留下来陪公子过夜。关于女人,波德莱尔偏于重口味,千金小姐、文艺女青年之类的,难入波哥法眼,波哥说:我只可能接受两种女人:妓女或者愚笨的女人,情人或者厨娘——兄弟们啊,这还需要理由吗?口味之重,简直令人目瞪口呆,喜欢妓女者尚可以理解,喜欢厨娘就实在令人匪夷所思。你别以为这只是说说而已,波哥的确喜欢过一个厨娘,并为此写下好几首诗。但是,这里的女人只与性有关,与爱情很远。波哥要的只是性伴侣,而不是真正的生活伴侣。
关于爱情,波哥说,爱情之所以令人厌烦,是因为这是一桩我们无法免去同谋角色的罪行。对波德莱尔来说,信仰方面的欠缺使得波哥将爱情与责任相互对立,无法摆脱原罪感,欲望和情感的疏远,感官和精神的冲突,徒增他的焦虑不安和辛酸。他把身体给了黑白混血女人让娜·迪瓦尔,把精神给了萨巴蒂耶夫人。如果把让娜启发他灵感而写下的那些诗比作激流的话,波德莱尔献给萨巴蒂耶夫人的诗篇就宛如一股股泉水。
或许这就是天才,有着迥于凡人的爱好,要么不来,要来就来点特别的。总而言之,波哥对于女人的这等爱好,让多少风流才子情何以堪!以至于在母亲和继父的眼里,他自由放荡的生活不合时宜,想方设法对他加以约束,这自然又增加了他同家庭间的冲突和矛盾,他在家里感到孤独,继而在学校里,在社会上,孤独缠上了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