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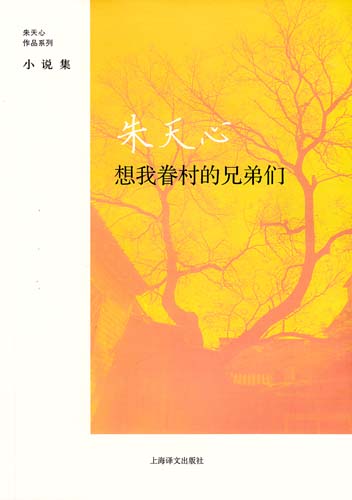 上海译文出版社前几年出了四本一套台湾当代女作家朱天文的作品,眼下又出版了朱家另一位才女、妹妹朱天心的三部,分别是《古都》、《二十二岁之前》和《想我眷村的兄弟们》。作家阿城曾说过,“朱家一门两代三人都是好作家,这在世界上是少见的。” 上海译文出版社前几年出了四本一套台湾当代女作家朱天文的作品,眼下又出版了朱家另一位才女、妹妹朱天心的三部,分别是《古都》、《二十二岁之前》和《想我眷村的兄弟们》。作家阿城曾说过,“朱家一门两代三人都是好作家,这在世界上是少见的。”
从王德威评“自80年代末期以来,小说家朱天心开始营造她的老灵魂世界”始,“老灵魂朱天心”这样的说法已成为她固有的标签。与其姐气质上的“仙气”不同,妹妹是人间的,但即便是人间的,也是人间少有的,因而再让人疑惑的是:如何娃娃般的面孔底下却藏满了阅人述事的老辣苍凉?
《二十二岁之前》都还是些聚拢她那天真烂漫遐思的散文,是《击壤歌》的余音、副歌,甚至是一遍又一遍的重唱,如《闲梦远,南国正芳春》:“‘……年轻人轰轰烈烈的抱负,是一场洛阳三月花如锦的繁盛,然而,花儿终究是要谢的满山满谷的,成就的人们是些晚熟的花儿,虽是万绿丛中一点红地矗立枝头,但终不免有些许孤单清冷和惘然,而且还是要落。’结论是,既是富贵荣华原一梦,我是连过程都不想要了。”
“连过程都不想要”,自是爱看《拿破仑情史》的小女孩一枪头的自说自话,却可从中窥见她字间零落的大风气。待从头,拾零落,收复旧河山,遂《古都》必然成为她文学野心乍起的重要作品之一,并位列“20世纪百年百部最佳中文小说”。天长日久阅过无数小说开篇,如马尔克斯,令人念念不忘的“多年以后……”句式,也同样难忘少女时期殷殷质问的语气,“难道,你的记忆都不算数……”及后面多个“那时候”:“那时候的马孔多是一个二十户人家的村落,泥巴和芦苇盖成的屋子沿河岸排开……(《百年孤独》)”这竟是与川端康成叠名对记忆的考问,故意的错乱,失落的符号?还是建立在“那时候”——那时候,马孔多没有被飓风吹走、消逝;那时候,一切都是不同的。
也许,从来重要的就是“古”而非“都”,是“时间”非“地点”。《想我眷村的兄弟们》则是“古都”的“落实”,不再是记忆式凭吊,而是工笔画现实。“用妈妈的百雀羚面霜抹成《岸上风云》中马龙白兰度的发型”、“那些个乘凉或看《晶晶》连续剧”、“五十年代,嫁黑人嫁GI去美国的”,那些与眷村有关的全局,充满年代符号的具象世界,时常能“在人群中乍闻一声外省腔时所顿生的乡愁”。如此如彼,都教你记起了你心中肆意无边的狂野,他想起他60年代嬉皮士的靓衫异步,你想起你坐在谷仓听妈妈讲过去的事,“他城与我城”不断互换,绝不仅仅是“想象的乡愁”。
骆以军析天心《古都》一段,恰也似暗指《想我眷村的兄弟们》,“对于‘外省’(眷村)这一逐渐被新挖掘/复写的历史淹覆成‘想象社群’的记忆——缝补、错置、成为不可能表象之记忆。”事件的变迁,地点的轮替,政治的花斗,时间的角力,是朱天心作品一再对自己狠心的创述。难怪胡兰成要讲“现在有了朱天心,要来说明李白真方便”。不知者光看起头句,便吓大了,不疑他“哗众取宠”才怪,其实到底是想说“风起的时候他又想飞了,像小虾”罢。
同样如“三三”旧友丁亚民叹天心,“张爱玲有所谓‘云端上看厮杀’,而你是偶一顾盼,便见生,便见死,照见人世,而你仍是干净清爽如天地不仁。”这“天地不仁”倒合了阿城讲“天心的强悍,即在于不饶”。父亲朱西宁曾说,“唯觉天心大得造就于礼乐教化,始有今日这番大志与成全;其作品也因之而绝非标榜现代而实则西化的时人所能忘尘。”对中年的朱天心而言,想必父亲的谆谆教诲尚尤在耳,而她也已到了念顾女儿萌萌的熟龄,说起来,《学飞的萌萌》不也是当年想飞的小虾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