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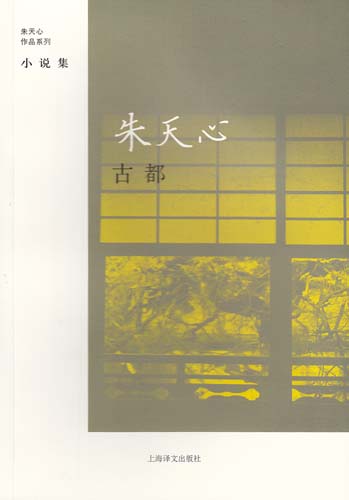 也许是千百年后吧。文明升沉,万事播迁,五洲板块又是几度震荡后,有个曾叫台湾的岛屿依稀残存。朔风野大,天地洪荒,早已闐无人烟的台北,或还残存当年一二繁华遗迹?沿着昔日二二八纪念公园旧址行来,荒烟迷漫,鬼声啾瞅。掘地三尺,哪还有半点尸骸。倒是千百页尚未腐化尽净的断简残篇,成为对某个世纪书市文化的最后见证。 也许是千百年后吧。文明升沉,万事播迁,五洲板块又是几度震荡后,有个曾叫台湾的岛屿依稀残存。朔风野大,天地洪荒,早已闐无人烟的台北,或还残存当年一二繁华遗迹?沿着昔日二二八纪念公园旧址行来,荒烟迷漫,鬼声啾瞅。掘地三尺,哪还有半点尸骸。倒是千百页尚未腐化尽净的断简残篇,成为对某个世纪书市文化的最后见证。
一阵腥风吹起那些书堆,噼噼啪啪,你仿佛听到阵阵歌哭之声:“昨日当我……”、“想我……”、“我记得……”。是老灵魂的声音么?穿过死生大限,它还是阴魂不散!世事混沌不清,世事又全如所料。在历史废墟间,老灵魂行徘徊,不忍离去——一切早都关灯打烊了,它还在摸黑找些什么?
自八〇年代末期以来,小说家朱天心开始营造她的老灵魂世界。阅人述事,洞若观火,笔调则如此老辣苍凉。从《我记得……》到《想我眷村的兄弟们》,再到新作《古都》,朱的创作量不能算多,但每次出手,必然引起议论。读者或为她的题材侧目不已,或为她的“论文体”叙述啧喷称奇。但最不可思议的,还是她率团登场的老灵魂人物。老灵魂来自各行各业,穷通蹇达不等,但个个“先天下之忧而忧”。他(她)们悸惧衰老与死亡,却有穷究老与死的兴趣。他(她)们看来对一切都不在乎了,却比谁都更在乎一切。在朱天心的指挥下,老灵魂渗透你我之间,散播末世消息。人家希望、快乐,老灵魂暗自神伤;人家心灵改革,老灵魂心乱如麻。这真是群杀风景的人物。
而朱天心自己也是个老灵魂么?小说家和她的人物真得对号入座么?也不过就是十多年前吧,朱天心凭着《击壤歌》《方舟上的日子》等作,颂赞青春,风靡多少学子。几番周折,她竟抛弃同辈读者(如我等),决心先自行老去。但她老得并不彻底,她还有话要说。过分老于世故的人其实写不出像《想我眷村的兄弟们》《匈牙利之水》这样的作品。是犬儒,也是天真,朱天心的作品因此形成一种风格的时差。这也许可作为我们进入她“老灵魂学”的一个门径。
一、与历史怪兽搏斗
朱天心作品最重要的特色是对时间、记忆,与历史的不断反思,而她老灵魂式的角色成为启动此一反思行为的最佳媒介。老灵魂生年不满半百,心怀千岁之忧。他(她)们知道太平盛世其实隐藏了无数劫毁的契机,也惊讶在死生大限之前,凡夫俗子竟能活得如此浑然无知觉。今朝欢乐,明朝枯骨,生命的必然与偶然,不就是一线之隔。虚空的虚空啊,一切的贪痴嗔怨,总要归于徒然。老灵魂独探死生的幽微逻辑,夙夜匪懈,且啼且笑,于是有了不能已于言者的冲动,有了书写的欲望。
论者可以轻易指出,老灵魂的忧虑就算事出有因,毕竟是有闲阶级的玩艺儿。芸芸众生未必真傻到不知生老病死,然而眼前的“近忧”都照顾不来了,还谈什么远虑?朱天心的人物都犯了一个毛病——杞人忧天。朱天心要不以为然了。她可反驳她的老灵魂其实个个胸无大志;他(她)们所关心的就是眼前的芝麻绿豆。一般人自谓看近难看远,说穿了,看得还是不够近。谁能想像这一分钟的家常,埋藏了下一分钟的什么噩耗?老灵魂事事关心,事事担心,他(她)们活得好累,也是不可救药的现实主义者。
朱天心折冲于最细密的现实关怀,以及最迂阔的生死忧思间,形成了她作品中的一大吊诡。照道理说,已经看到死亡另一面风景的老灵魂,还有什么心情斤斤计较浮世人生?但我以为这一吊诡是她叙事风格的基础,也与她想像历史的方式息息相关。看她的作品,尤其像《预知死亡纪事》及《拉曼查志士》等,不由你不觉得她笔下人物优生忧死,已迹近妄想狂的征兆。“人有旦夕祸福”真是他(她)们的座右铭。有幸死得其愿、死得其所的人毕竟太少。为了“走得”干净,老灵魂们上自生辰八字,下至内衣内裤都得事前交代打点。但欲洁何曾洁,只怕生命中的琐碎让我们活得谨小慎微,死得也不明不白。《“预知”死亡纪事》,顾名思义,已充满自我解嘲玄机。死亡如果是一了百了,哪由得我们预知后事?生命是如此嬗递紊乱,怎能叙述纪事?老灵魂是在打一场看不见敌人的仗,其虚张声势处,恰如四百年前的堂吉诃德一般。
朱天心及她的人物一方面苦于世事无常,一方面又贪婪的吞吐千百种过眼资讯,成为一种文字反刍奇观。读者或要为她益趋漫漶的风格所苦,因为她越来越不能讲个一清二楚的故事。但换个角度,朱天心放弃传统定义的故事性,几乎是理所当然的事。借此她反可能逼近现实无明也无常的面相。她的琐碎议论姿态成为对抗历史大说的方式。所谓本末倒置于她或有新解。当事物的“本”已无所可本,我们所能有的也只是枝微节末。正因为朱及她的人物意识到大历史的了无理性,他(她)们对生活的细节,对记忆的缝隙,愈发变本加厉的摩挲思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