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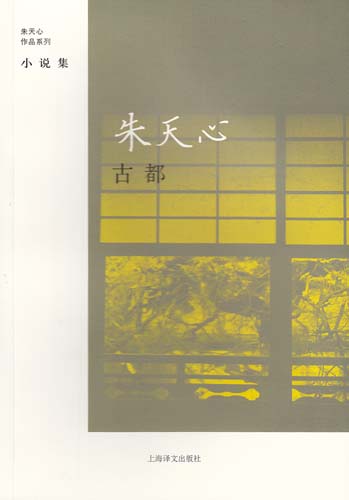 读台湾作家朱天心近期的作品,尤其是像《想我眷村的兄弟们》(一九九三)和《古都》(一九九七),可以说是件让评论家很为难的事情;道理很简单,因为朱天心把话里外都说尽了,而且说得有声有色,有根有据。不管是后现代后结构也好,马克思商品理论也好,虚构的方法和技巧也好,都被写进了她的小说中去。这番耐人寻味的“理论自觉”,首先表现在她的叙事内容和对象上,更可以从她极富后设(或者说元虚构[metafiction])意味的布局和叙述中观察得到,以致她的小说叙事和理论论述间出现了一种亲密的互为译文的关系。而如此一手创作、一手点评的饱满状态往往会搞得评论家多少有些手足无措,甚至不无黔驴技穷之窘。 读台湾作家朱天心近期的作品,尤其是像《想我眷村的兄弟们》(一九九三)和《古都》(一九九七),可以说是件让评论家很为难的事情;道理很简单,因为朱天心把话里外都说尽了,而且说得有声有色,有根有据。不管是后现代后结构也好,马克思商品理论也好,虚构的方法和技巧也好,都被写进了她的小说中去。这番耐人寻味的“理论自觉”,首先表现在她的叙事内容和对象上,更可以从她极富后设(或者说元虚构[metafiction])意味的布局和叙述中观察得到,以致她的小说叙事和理论论述间出现了一种亲密的互为译文的关系。而如此一手创作、一手点评的饱满状态往往会搞得评论家多少有些手足无措,甚至不无黔驴技穷之窘。
朱天心对这种兼叙兼议的散文风格(又有人称之为“百科全书小说”)(骆以军)的操作,在《古都》这部中篇里达到了挥洒自如、炉火纯青的境地。但《古都》的真正动人之处,又并不完全来自这种反讽性的、自我拆解的叙述策略。在这里,朱天心整个的语调是抒情性的,笔法是内省询问式的,目光则是忧郁型的;在“中年怀旧”这一大情感结构下,在在表现的是弥天的悲情,流露的是对集体的和个人的历史失忆症的恐惧。缘起于一场对当代日益陌生的台北的铭心刻骨式凭吊,这篇关于无名的“你”的叙述,以缝合个人心理创痛为目的,但同时致力于开拓深远的历史想像空间,并且毅然把我们引入了一个庞大错综的都市潜意识区:这正是朱天心近期决心以人类学家的姿态“重新探险台北城市”的原始动机和归宿,也是小说《古都》的感染力和美学及认知价值所在。
在进一步解读《古都》及其政治潜意识之前,我想提及一下我读朱天心时一个挥之不去的感觉,那就是她与大陆作家王安忆有很多可媲美之处,尤其是与王安忆近年以《长恨歌》为代表作的一系列“伤心的故事”(包括《香港的情与爱》,《乌托邦诗篇》和《伤心太平洋》等)分担着极其相似的历史忧郁感。甚至在叙事的自我意识和反讽机制这一层面上,朱天心的《威尼斯之死》(一九九二)和王安忆的《叔叔的故事》(一九九○)这两个中篇也都表现出令人惊叹的遥相呼应。
如果在纵深的历史谱系上,阅读朱天心及其姊姊朱天文的文字时,离不开回眸将苍凉凄美视为永恒的张爱玲,那么在一个横向的历史联结上,朱天心和王安忆也许都在书写一个不再年轻、不复有激情的时代;中年人那种日渐压抑下来的对向往的向往,以及对现实孤绝的叩问,成为这两位几乎同龄的作家共同的叙事视角和抒情起因。她们同样以一种兼叙兼议的笔触探索人物的内心世界,当代城市(台北和上海)同样成为她们探索历史和记忆的一大场景,甚至连她们的创作历程,都可以说有某种相互映照的由简而繁的同步变奏。而朱天心王安忆各自的关怀角度和叙述对象之间的差异,则无疑给我们这个时代与其历史脉络提供了一个很贴切的注释。在当代台湾文学与大陆文学之间,尤其是两岸各自的城市文学之间,实在是很有进行比较文学研究的可能和必要。相对与常常沦为大而无当、或者不关痛痒的中西比较文学而言,就同一种语言的两种文学形态进行历史的对比参照,在我看来是大有可为的一项学术事业。
不过这话扯得有些远了,希望以下结尾处能再收回来。这篇以读《古都》为主的文章并不可能将朱天心和王安忆做一番系统的比较,但贯穿两位作家近期作品的忧郁意识和哀悼之情,揭示的也许是她们共同分享的历史情境,是她们对历史经验与记忆极其相似的探寻和挪用。
朱天心所悉心探寻的是台北这座见证了荷兰殖民者、明清朝廷、日人半个世纪的占领、国民党统治、直至解严后新党政争的饱经沧桑的历史名城;同时她也以极其私密、喃喃耳语式的内心对白反照出一个都市人眼中密密麻麻、层层迭迭的生存空间,一个不断引起伤痛、激起想像和回忆的现代大都会。主人公“你”显然是一位来自中产阶层的抑郁的中年女性,置身在当代台北纷繁诡谲的街头风景里,她深深觉得二十年的扩建拆迁改变了她生于斯长于斯的城市,使她觉得一如流离失所的外乡人,也使她不得不追抚灿烂的青少年往事,几近绝望地仰天叩问:“难道,你的记忆都不算数?”而日益高涨的本土化情绪和造势,更使得寡言的她“从不停止的老有远意、老想远行、远走高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