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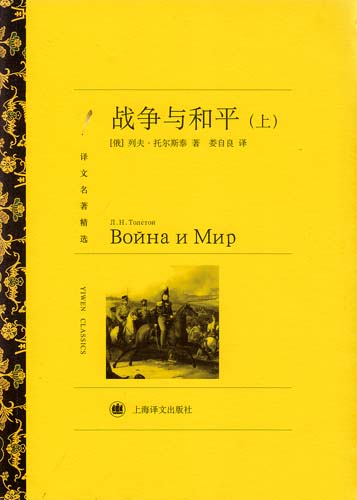 中国译坛有一个怪现象,就是经典著作重译本多。上世纪九十年代,多家出版社、多位译者似乎铆足了劲,好像在比赛谁翻的《红与黑》更好,仅我个人庋藏的中译本,就有六七部之多。结果,好像也没评出个高低优劣,宝贵的资源就这样在重复劳动中流失了…… 中国译坛有一个怪现象,就是经典著作重译本多。上世纪九十年代,多家出版社、多位译者似乎铆足了劲,好像在比赛谁翻的《红与黑》更好,仅我个人庋藏的中译本,就有六七部之多。结果,好像也没评出个高低优劣,宝贵的资源就这样在重复劳动中流失了……
中国译坛有一个怪现象,就是经典著作重译本多。上世纪九十年代,多家出版社、多位译者似乎铆足了劲,好像在比赛谁翻的《红与黑》更好,仅我个人庋藏的中译本,就有六七部之多。结果,好像也没评出个高低优劣,宝贵的资源就这样在重复劳动中流失了。当然,说重译是重复劳动有点不公道,即便是重译,每位认真的译者在迻译时还是花了大量心血的,对翻译一道稍有接触而不一定懂法文的人,都知道罗新璋的译本比起罗玉君的译本是有进步的,问题是这样短时间内的“疲劳轰炸”,究竟能收到多大的审美效益?
十几年过去了,《红与黑》热已过去,敢问人们消化得了这些译本吗?回答只能是否定的,这与重复劳动何异?倘若人们把出版《红与黑》的人力和物力花到别的还没有中译的文本上,例如多卷本的《龚古尔日记》,对于读书界是否更有益处呢?时至今日,大概不会有哪位真想干点实事的翻译家会凑热闹,再去迻译《红与黑》;但是,重译托尔斯泰,重译陀思妥耶夫斯基,重译屠格涅夫,似乎其风未戢,尽管像《红与黑》这样一哄而上转眼出了十多个中译本的现象已一去不复返。我在网上略一检索,仅1978年以来,印行过的《战争与和平》就有高植、董秋斯、刘辽逸、草婴、张捷、娄自良的译本,这些都是名牌出版社的出版物,译者都是名家,其中也不无汰旧布新的意义,某些从英文转译的译本,今后可能不会重印了,但是重译还是多了点。须知有大量有价值的外文书仍有待翻译家(更准确些说是出版家)的“青眼”,更多的读者亟盼读到更多著作的中译本。
有某出版社的编辑曾让我开出一张翻译书目,我随手把常置桌边的几本书名抄了给他,因为深知自己所爱读的书太僻,没什么市场,不能为出版社取得效益,故而没把这事当真。不出所料,书目寄出后有如石沉大海,但我还是有点心有不甘,想在这儿再谈一下。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大陆比较文学之风大盛,可惜无论见之学刊或论文集,有太多的论文仍属于开蒙阶段,如论《西厢记》与《罗密欧与朱丽叶》之异同之类即是。尽管也有人想到要切切实实译几本比较文学的经典著作,作为内地学人开展研究时的借鉴,但限于学力和视野,成效不彰。其中苏联学者日尔蒙斯基的专著《拜伦与普希金》,始终未能译成中文。这部书不容易译,难点在于除对普希金须有专门研究外,还要对拜伦有常识以上的了解,书中征引的拜伦诗作最好从原文译出。
如果容我挑选的话,诗人穆旦应该是译此书的最佳人选。穆旦已矣,译《战争与和平》的翻译家们,难道就匀不出一两位来译此书?谈到拜伦,枕边常放着一部英国学者莱斯利·马钱德的经典传记《拜伦:一幅肖像》。马钱德毕生专研拜伦,编有十二卷本的《拜伦书信和日记》,《肖像》是从他早年三卷本的《拜伦传》删削浓缩而成,其学术水平远在内地市场流传的几种拜伦传之上,但据我所知,直至目前为止,还没听说有哪位翻译家对此感兴趣,甚至谈及者也寥寥可数。不同于俄国文学,英国文学在我国始终热度不减,总不成英国文学的毕业生都重译《傲慢与偏见》去了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