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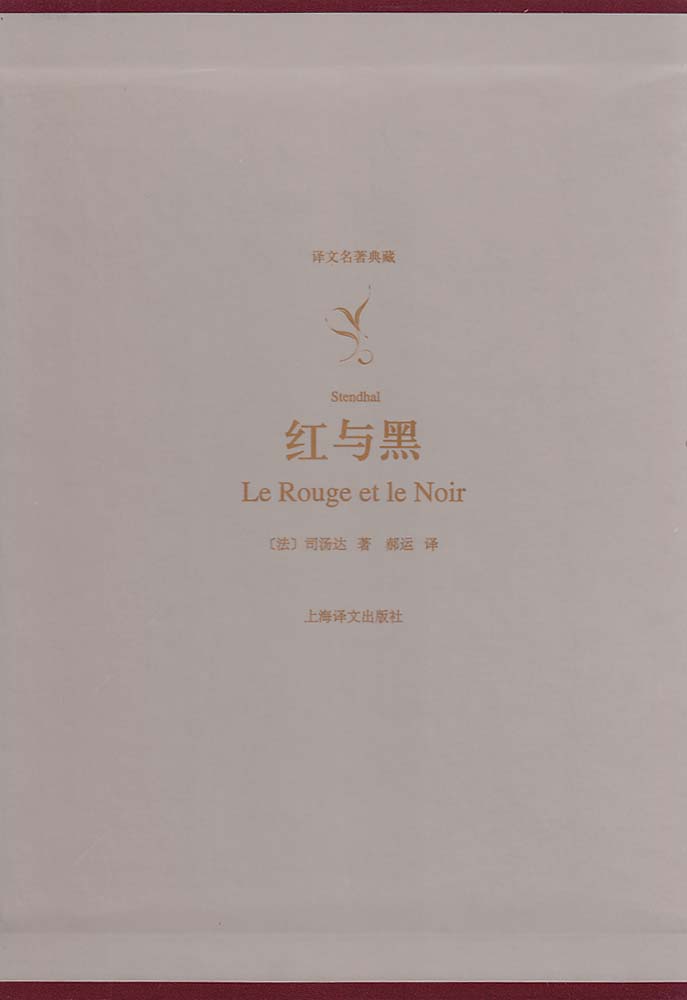 报复 报复
整个春天,他们围在窗前,看无尽的美景—月光一样流动的河水、人迹罕至处长出的嫩草、青色的山脉,还有一块糟糕的泥田。整个春天,他们都在议论那头蠢牛和比它更蠢的农夫,他和它将石块翻进泥田,而不是翻出来。
入冬时,他们找到农夫。后者抓起一把陈米,将它们一粒粒地漏进他们早已伸过去的帽子里。
“你得确保你心里没有在说,要不是风调雨顺,老天帮忙,他怎么能收获到粮食—”农夫捏住手中的米。
“我们确保。”
“你得确保你心里在说,我再也没见过像他这么伟大而慈悲的人了。”农夫开始让米重新漏下去。有一些自尊心过强的人因此走掉。极个别的人索性就没来,饿死事小,求人事大。
残忍种种
据波德莱尔说,有时很有教养的人会突然做出很残忍的事情。我小时应该是有教养的,不能爬树,不能游泳,不能打架。但在午睡起来时,我会手持一枝粉笔,蹲在诱饵旁边,耐心等待艰难爬上水泥台阶的蚂蚁。蚂蚁总是挺着硕大的头颅,埋头直线前行。那些细小的爪子像风车一样,令人眩晕地前行是的,就在它抬头确定了诱饵存在时,我拿粉笔在它周围画了一个没封口的圈。
蚂蚁沿着圈的边沿行走,一早就丧失跨越边界的勇气。当它发现出口时,大约和我一样欣喜。我的爷爷会给我讲一些古代兵法,倘若把四面城墙围得水泄不通,守城者必定鱼死网破,所以必要留个活口。多年后,我想,那些守城的人可能就死于那上帝施舍的希望。蚂蚁在逃出来后,遭遇鬼打墙。我像万能的作家,随意画出它行走的路线,然后看着它带着生存的希望,勤勉奔波。
我让它走了很久,一直走到我手腕和腰部都酸了。我站起来,踩死它。没有噗哧的声音,没有鲜血飙出来,世界安静得像一颗零。一只蚂蚁变成一颗黑色粉尘,它将和鸡屎一起被笤帚有力地扫出人们的记忆。
波德莱尔说,“我”看到正午的楼下有位汗流浃背的玻璃匠,便招呼他上楼来谈谈,他就小心翼翼地背着那易碎的生计上了楼最终,玻璃匠被训斥,因为他竟然没有一块有颜色的玻璃。这位惶恐的生意人只能又小心翼翼地背着他的全部生活来源下楼。
在他胜利走到楼下时,“我”抛出一个花瓶,把他那些捆好的玻璃砸碎了。
那声响,像一座水晶宫被炸毁了。
还有就是皮兰德娄,其小说《太阳与阴影》云,一中年男子准备去投海。但在马车到达海边时,他被一个热情好客的朋友发现并强拉下来。朋友问他来干什么—你见过这难堪的问题吗,他能说,兄弟,我要去死吗?他支支吾吾。朋友便带他去游泳。想想,自杀还来得及,先演习下也没什么不好。他就这样怪异地进入海里,原来水是这样的冰冷。然后,就是喝酒,朋友的朋友,林林总总来了一二十个。大家便醉了。然后回家。
故事的结局有点意外,他在口袋里摸索着,忽然摸到毒药。服毒本是被他排斥过的死亡方式,但他还是匆匆吃了下去。他咬着牙,度过腹部的绞痛,死了。
囚犯在进监后会被收缴皮带,因为可能用来自缢。剥夺自由包括剥夺自杀的自由。
我最早阅读的外国小说之一是《红与黑》。于连代表着强悍—扼住生命的咽喉,朝上流社会不择手段前进,如此等等。我按照乡、县、市、省、首都的规划强力前行,我不要死在双港河那温柔的河水里,我不要那些可怜的庄稼人拿出皱掉的香烟敬给我,我不喝你们造的谷酒,不吃你们送的腊肉。我不稀罕那瓷器般的天穹,和漫天的星斗。
我装载着那些落魄秀才的酸痛,那些剽悍山樵的惶恐,自怜得像一只老鼠,开始沿着街市的墙角,慢慢而小心地往闹市中心靠近。
我有时感觉自己是秀才,背着雨伞。在一部关于毛泽东的电影里,他背着油纸的雨伞,用去农村的方式去城市。我用去城市的方式去城市。
我感觉自己感冒咳嗽,孤苦伶仃,不敢多看一眼路边的村姑,多饮一杯小酒,我跋山涉水,披星戴月,沿着一条官道走到首都。我在老鼠蹿来蹿去的旅馆里吃着粗糙的面食,头悬梁,锥刺骨,苦读四书五经,苦等吾帝放榜开考。
但是有那么一两位学长拉着我去京郊寺庙,说那里不定有个什么艳遇——还都是上流社会的太太小姐。说来也巧,我一去就撞见。也可说是王昭君,也可说是关之琳,总之一位貌若天仙、天性善良的女子用温柔的眼,勾走我。
我一路小跑,一路等待那夫人从马车里探出头来,对我妩媚一笑。我就这样丢魂丧魄,一路跟到一个幽宅。她进去了,还望我一眼我跟着推门而入。结果是一只鞋尖从天而降,踩灭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