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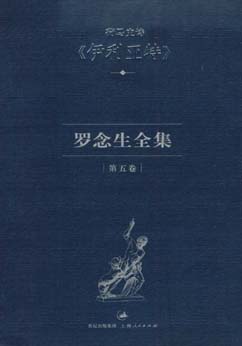 年轻时因为写了几篇小说,混了个作家的头衔,顺便也结识了一些同样做着文学梦的青年作家。既然做着相同的梦,大家便不时小聚一回,谈谈各自的作品,谈谈圈子里的事情和圈子外的新闻,有时也会讲一些笑话,包括黄色笑话和政治笑话。 年轻时因为写了几篇小说,混了个作家的头衔,顺便也结识了一些同样做着文学梦的青年作家。既然做着相同的梦,大家便不时小聚一回,谈谈各自的作品,谈谈圈子里的事情和圈子外的新闻,有时也会讲一些笑话,包括黄色笑话和政治笑话。
自然大家也会谈到一些外国作家,谈得最多的是谁,我已经忘了,反正不外乎20世纪的著名作家或时髦作家;间或也会谈到19世纪的作家,但在我们眼中,他们差不多都过时了,都落伍了。例如我们可能会大谈一位叫卡佛的美国作家,而对另一位比他伟大得多、公认的现代短篇小说之父却视而不见。这种情景与上世纪80年代的作家大谈秘鲁作家鲁尔福或巴西作家罗萨倒有点相似。至于19世纪以前的作家,至于遥远的希腊作家,尤其是那位将近三千年前的荷马,则从未听谁提起过。我们只顾埋头写自己的东西,就当他老人家根本不存在似的。历史上可能并无荷马其人,但这里的不存在指的是,这位“来自山石嶙峋的基俄斯的盲人”连同归在其名下的两部作品都不存在。
但由罗念生、王焕生翻译的《伊利亚特》就在我的书架上,且在那里放了好几年了。自然,它是不会自己长腿跑到那里的,也不是别人赠送的。它就是我花钱买的。买来了,放在书架上,但就是不看。不看,是因为它早就过时了,是老什子的老什子了;不看,是因为它是原始部落口口相传的产物,现在已经是互联网时代了;不看,是因为远古的艺术必定是粗糙的丑陋的,就像远古的石器一样;不看,是因为它肯定是无法卒读的;不看,是因为周围搞写作的人都不看;不看,是因为不但中国人不爱看,好像老外们现在也不爱看—据说“荷马之死”紧随着“上帝之死”俨然已成定论;不看,是因为有些如雷贯耳的著作可以不必亲自去读,例如学经济的不必去读斯密的《国富论》,学物理的不必去读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学生物的不必去读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等等;不看,是因为表面上满不在乎的我们,心里头其实对他怕得要死,不把他视为同类,甚至不把他视为人类中的一员;不看……尽管谁都清楚,我辈是必朽速朽之人,此君则在永垂不朽之列;需要强调的是,两种人根本不能相提并论,用歌德的话说,连给此君提鞋都不配。
但我知道历史上有一些人将荷马史诗读得很有名,马其顿的亚历山大是一个著名例子,据说在其疾风骤雨般的征服生涯中,《伊利亚特》一直是他的枕边书。对于尼采,荷马创造了甚至令最伟大的天才感到沮丧的作品,其中矗立着可供后代景仰的不可逾越的形象。我还知道许多伟大作家如维吉尔、但丁、弥尔顿、歌德、陀思妥耶夫斯基等对荷马极为赞赏。就我有限的了解,托尔斯泰和济慈的例子似乎尤其值得一提。托尔斯泰初读《伊利亚特》时是有保留的,后来他学会了希腊文,读到了原汁原味的《伊利亚特》,才大呼过瘾,并认为翻译的荷马与真正的荷马,其差别犹如“冒着蒸汽的沸水之于冷冽的泉水,后者虽然冷得令人牙齿发痛,有时夹带着泥沙,但它受到阳光的照射,晶莹闪亮,更加纯净,更加甘美”。但并非人人都可以像托翁那样直接品尝原著,且即便会希腊文,也未必有他老人家那样的感受力。诗人济慈读的就是查普曼(G.Chapman)的译作,且把他的感受写入诗中。查普曼是第一个让荷马说现代英语的人,他的译作被后人认为华丽有余而质朴不足,但这并不妨碍济慈先生读得如痴如醉:就像观星学家发现了一个新的星座,就像科尔特斯发现了太平洋。对于一位能够感觉到鲜花在自己身上生长的诗人,我怀疑这些比喻能否道出其真实感受的十分之一,所以我们应该把济慈本人的感受而非任何其他比喻作为一个参照系,就像历史学家把阿基米德的裸奔和大喊大叫(他喊的是“尤里卡”这个词,如果你不解其意,可以径直把阿老看成是现代行为艺术最古老和最伟大的先驱)作为科学发现时刻的参照系一样。事实也是如此。当凯恩斯的著作传入美国时,当时的青年经济学家的领袖萨缪尔森就把他们读《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心情与济慈读荷马史诗的心情相比较。尽管如此,我还是不必去读《伊利亚特》,原因也很简单:我既不是托尔斯泰,济慈,雅斯贝尔斯,也不是什么青年经济学家的领袖……再说一遍,也不配给这些人提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