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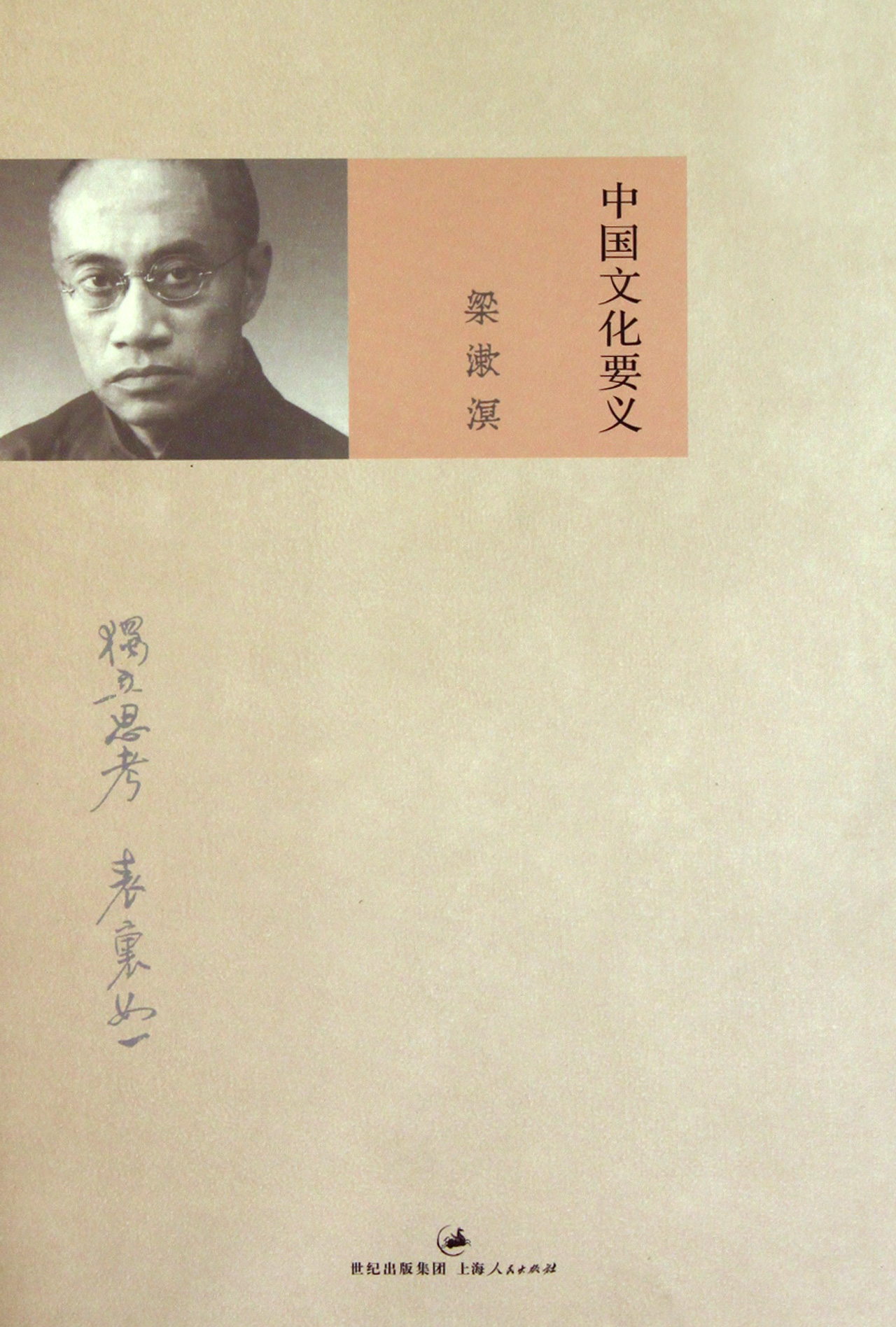 世纪文景迄今已出版了《中国文化要义》、《乡村建设理论》和《人心与人生》梁漱溟学术著作3种,以及《罗念生全集》11册。而梁漱溟和罗念生两位大师作品的整理和出版都离不开他们后人的工作,对于梁漱溟的儿子梁培宽、梁培恕和罗念生长子罗锦鳞三位来说,他们的人生晚年与父亲一生的思想和工作联系在了一起,这是传家也是守望。昨天,梁培宽、梁培恕和罗锦鳞齐聚北京,一起谈论他们这二三十年的文化守望工作。 世纪文景迄今已出版了《中国文化要义》、《乡村建设理论》和《人心与人生》梁漱溟学术著作3种,以及《罗念生全集》11册。而梁漱溟和罗念生两位大师作品的整理和出版都离不开他们后人的工作,对于梁漱溟的儿子梁培宽、梁培恕和罗念生长子罗锦鳞三位来说,他们的人生晚年与父亲一生的思想和工作联系在了一起,这是传家也是守望。昨天,梁培宽、梁培恕和罗锦鳞齐聚北京,一起谈论他们这二三十年的文化守望工作。
梁家与罗家,他们都曾有一个世人视为“国宝”、“大师”的大人物作为家庭中心。虽然斯人远去,但遗风犹存。
梁培宽:整理中了解父亲
已故学者、国学大师梁漱溟生前主要研究人生问题和社会问题,堪称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著有《中国文化要义》、《乡村建设理论》、《人心与人生》等重要著作。1980年后相继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委员会委员、中国孔子研究会顾问、中国文化书院院务委员会主席、中国文化书院发展基金会主席等职。
梁漱溟长子梁培宽,退休20余年,一心只为整理父亲梁漱溟的文字,编辑出版了厚厚8卷本的《梁漱溟全集》和几十种单行本。1986年退休后,梁培宽开始整理父亲梁漱溟的著作,前后一共做了25年之多。梁培宽原来学的是生物,对父亲梁漱溟的东西一点都不懂,“我曾经找父亲谈话,我就说,你给我简单地、深入浅出地讲讲佛学究竟是怎么回事儿,前后大概给我讲了两年,到现在我还整理不出一个印象来,不清楚究竟他说的是什么。我就是在这么一个情况底下进行工作的。”经过这20多年的整理工作,梁培宽也慢慢明白究竟做的是什么事,做了一件什么工作,它有什么意义,梁培宽说:“虽然他是我父亲,但是我原先对他的了解很远很远,是在这二十多年的整理工作中,觉得慢慢跟他走近了。所以这二十多年工作,实际上是我走近自己父亲的过程。”
梁培宽还开玩笑提到,以前出版父亲的作品很难,现在都抢着来谈出版事宜,对于这些整理出版的著作,梁培宽说:“父亲梁漱溟的一些著作或者一些谈话,当然不可能都是十分有价值的,但总不至于是毫无价值的,总会有一些值得保留的东西,总会有一些有意义的东西值得后人来研究、来思考。我现在做这个工作,就是设法把它整理出来,跟出版者合作,把它交回社会,提供给读者,送给图书馆,可以由更多的人来阅读。”
梁培恕:为父亲做传“说明他”
梁漱溟的次子梁培恕,从动笔撰写父亲的传记,直至最终出版,前后历时20年。他为父亲写传记与哥哥梁培宽对父亲作品的整理,梁家两兄弟共同的工作室是对父亲的精神遗产的传承、守护。
梁培恕昨天说,早在1986年,父亲还在世的时候,他就跟哥哥说将来需要替父亲写一本传记,“因为外界对他的误解、误传相当多,有些事情需要纠正,再一个对他的认识也有很大的距离,这些事情需要我们做,即便很勤奋细心地找材料都不能够体会,我们作为最近的亲属,有他的一些直接的感受,目击的东西,这个是不可以替代的。”而这二三十年来,梁培恕一直做的事情大概就是为父亲写作,“都在说明他”。
从1988年梁漱溟去世之后,梁培恕才开始从头阅读父亲的著作算起,传记也断断续续写了10年,这就是2011年出版的《中国最后一个大儒:记父亲梁漱溟》。在这本传记完成之后,梁培恕又写了《架桥人和他的梦》,这第二本父亲传记写的是梁漱溟的学术思想和政治活动,“他说他的使命就是在东西文化之间架一座桥,东方人也包括中国人其实不了解中国文化是怎么回事儿,西方人也不了解中国文化是怎么回事儿。” 梁培恕说,他现在开始写的另一本父亲传记叫《人类需要认识自己》,这句话也是梁漱溟书的一句话,是他在结束生命前留下的一种呼吁和警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