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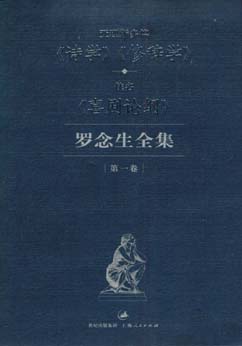 荷马史诗的世界是一个英雄的世界,充满了正义与责任兼备的神祇、巨人和英雄。史诗中不时出现的“箴言”,好似《圣经》里的金玉良言,总能让你停下来沉思片刻,产生很多共鸣,关于真理,关于生死,关于命运。荷马似乎时时在提醒着我们,他所经历过的辉煌过去,那时的人们拥有丰足的物产、五十个房间的宫殿、庞大的家族,当然还有超强的体能,以至于后来很多人禁不住猜测荷马对英雄时代的描述,是一个诗人对过去充满想象的重建和缅怀,《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两万八千行诗句,字里行间都闪现着荷马诉说不尽的怀旧情结。 荷马史诗的世界是一个英雄的世界,充满了正义与责任兼备的神祇、巨人和英雄。史诗中不时出现的“箴言”,好似《圣经》里的金玉良言,总能让你停下来沉思片刻,产生很多共鸣,关于真理,关于生死,关于命运。荷马似乎时时在提醒着我们,他所经历过的辉煌过去,那时的人们拥有丰足的物产、五十个房间的宫殿、庞大的家族,当然还有超强的体能,以至于后来很多人禁不住猜测荷马对英雄时代的描述,是一个诗人对过去充满想象的重建和缅怀,《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两万八千行诗句,字里行间都闪现着荷马诉说不尽的怀旧情结。
荷马史诗深深影响了整个欧洲文化传统,尤其是《奥德赛》,被看成是所有虚构文学类型的始祖,被视为欧洲的第一部小说。后来,到了古罗马时代,维吉尔成功地将《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主题交织,创作了他文学生涯的最高成就《埃涅阿斯纪》,此外,他还将赫西俄德的《田功农时》移植到自己的《农事诗》之中。桂冠诗人德莱顿曾翻译了维吉尔的所有作品,但他仅翻译了《伊利亚特》的第一卷,便直呼“其中的欢乐胜过翻译维吉尔的任何作品”。后来同为诗人的蒲伯更称赞“荷马是伟大的天才,维吉尔是伟大的艺术家”,并将《荷马史诗》与《圣经》并举,高度称赞荷马的原始性和历史真实性:“荷马是野蛮世界中最古老的作家,是古代世界唯一一面真实的镜子”。
后来,德国考古学家施里曼更是因着这份对荷马史诗并非虚构而是真实的坚持,发掘了特洛伊、迈锡尼和梯林斯,使得荷马笔下的英雄时代更加扑朔迷离。千百年来,荷马史诗长久而深远地影响了一批又一批伟大的作家、诗人、剧作家,其中有但丁、席勒、歌德、莎士比亚等等,无法一一尽数。
在古希腊文明的宝库之中,同样可以引发共鸣,展现生与死的挣扎、真理与命运的撕扯的,古希腊悲剧不可不提。亚里士多德曾在《诗学》之中专门探讨“悲剧”的含义,他认为悲剧的目的是要引起观众对剧中人物的怜悯和对变幻无常之命运的恐惧,由此使感情得到净化。《俄狄浦斯王》、《阿伽门农》、《被缚的普罗米修斯》、《特罗亚妇女》、《美狄亚》等诸多大家耳熟能详的名剧无一不在表现着“命运难逃”这一主题,也无时无刻不在彰显着看似弱小的可以“被主宰”的人所具有的可以撼动命运的力量。
读古希腊悲剧,想来就像自己随着剧中人物一起走了一遭,喜怒哀乐皆具,酸甜苦辣尝遍,一起哭一起笑,同生共死;又像是在剧中看见了自己,总是怔怔地望着剧中的那个自己,分不出究竟哪个是真哪个是假。将自己的生命融入剧中,再将剧中的自己拉出剧外,如此挣扎一番过后,发现自己也一点点地变新着,就像当下这个季节大树小树上那一点点往外冒着的新绿。两千多年以来,经典之于读者,这是最郑重的给予。
不禁又想起埃斯库罗斯的《波斯人》,这部现存唯一取材于历史题材、讴歌希腊人抵抗波斯人入侵、争取民族自由、抨击专制君主的古希腊悲剧,至今读来依然热血沸腾。这部剧由罗念生先生翻译,他在1936年《〈波斯人〉在中国出版序言》中写道:“本想译嗳斯苦罗斯的《阿加麦谟农》或《被缚的普洛麦秀斯》,但有一种力量鼓励我试译这个‘充满了战争色彩’的悲剧。当诗人制作本剧时,他心里怀着两种用意:第一种是净化人类的骄横暴戾的心理;第二种是激动爱国心,这两种用意很值得我们体会吧!”显而易见,以希腊人的爱国心激励当时国人的爱国心乃是罗先生的用意。
从清末到民初,国民一直在抗争,虽抗争对象不同,但救国图强的目标从未改变。在这一方面,我们和希腊的命运何其相仿!当其时,希波战争中誓死捍卫温泉关的斯巴达三百勇士成为鼓舞民众的典范,1902年,梁启超曾作《斯巴达小志》,1903年,鲁迅更以“自树”为笔名在《浙江潮》上发表文言小说《斯巴达之魂》。而敢于与强权抗争盗得天火的普罗米修斯,也成为时人争相歌颂的榜样。人人都置身于时代大潮之中,所需的是多一份情怀和担当。
罗念生先生曾在他的早年发表的诗集《龙涎》中,收录一首《东与西》的短诗,其中写着:“东与西各有各的方向,我的想象还在那相接的中央。”一百多年来,多少位前辈学者像罗念生先生这样,以在中华大地上传播古希腊罗马文明为己任,终其一生执著于对西方的探寻与想象,将西方古典文明的经典作品引介到国内,启蒙滋养国人,以期带来国人精神之大改变。他们有周作人、朱光潜、罗念生、谢德风、严群、林志纯、缪灵珠、吴于廑、杨宪益、杨周翰、水建馥、王焕生等,他们架起了东方与西方相互交汇的桥梁,传来了东方与西方相互交融的福音,居功至伟。
今日适逢罗念生先生逝世25周年,仅以此文敬献罗先生。我社即将推出增订典藏纪念版《罗念生全集》,向罗念生先生致敬。
先生远去,遗风犹存!罗先生千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