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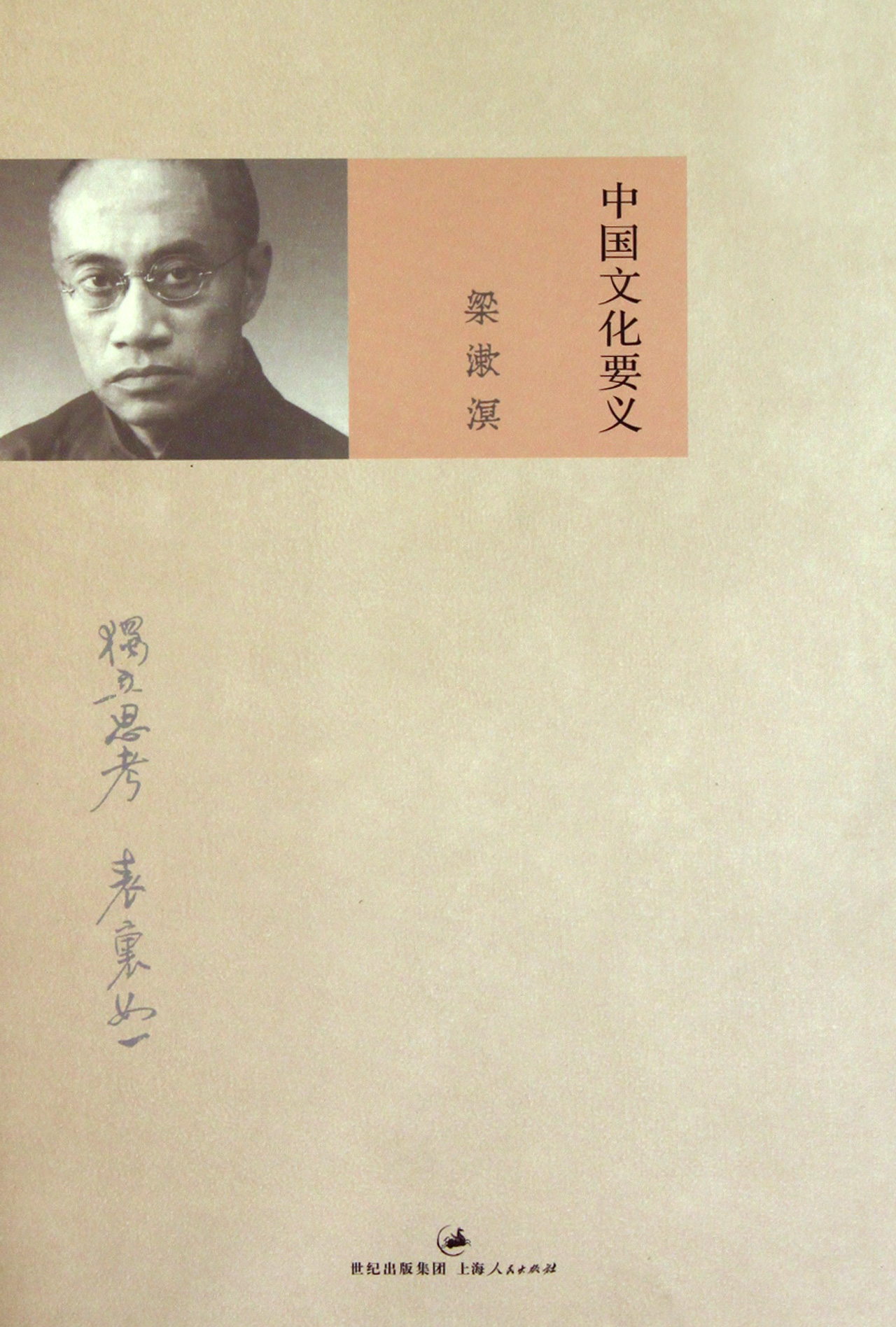 中国有两位大学者并不为人所熟知——其一梁漱溟,中国现代著名思想家、爱国民主人士,亦有“中国最后一位儒家”之称。但很长一段时间,他被贴上了“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反动知识分子”的标签。他曾自称“问题中人”,毕生为求解中国问题和人生问题思索与实践。对于佛学和儒学的关系,先是认为“惟有佛学的宇宙观和人生观是正确的”,继之认为“儒学适合于绝大多数人,而佛学只适合于少数人”,早年甚至想过出家。其思考凝聚为《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国文化要义》、《人心与人生》等思想著作。 中国有两位大学者并不为人所熟知——其一梁漱溟,中国现代著名思想家、爱国民主人士,亦有“中国最后一位儒家”之称。但很长一段时间,他被贴上了“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反动知识分子”的标签。他曾自称“问题中人”,毕生为求解中国问题和人生问题思索与实践。对于佛学和儒学的关系,先是认为“惟有佛学的宇宙观和人生观是正确的”,继之认为“儒学适合于绝大多数人,而佛学只适合于少数人”,早年甚至想过出家。其思考凝聚为《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国文化要义》、《人心与人生》等思想著作。
另一位知名学者是古希腊文学翻译家罗念生。他曾被称为“一个中世纪的和尚”,因为据说“只信希腊教,希腊就是他心中的上帝”。他自1929年与古希腊文学一见钟情,至1990年去世的61年来,心目中只有“古希腊文学”这一单纯主题。也因此穷毕生之力完成了近千万字的翻译和文论,作品汇集为11卷《罗念生全集》。
梁漱溟的《人心与人生》、《中国文化要义》、《乡村建设理论》等重要作品以及古希腊翻译家罗念生的《罗念生全集》皇皇11卷,都曾在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下属的北京世纪文景公司出版。日前,“世纪文景”分别邀请梁漱溟之子梁培宽、梁培恕及罗念生之子罗锦鳞,讲述“传家与守望:父辈梁漱溟、罗念生的过往旧事”。
梁漱溟:在佛教和儒学中求解人生
梁漱溟是中国知识分子中一个最为纯粹的人。他曾说“人生不好说目的,因为目的是后来才有的事”,又说“人生的意义在于创造”。人生的创造,在他眼中有两个方面,一是很显著的创造,别人都看得见,叫“成物”;另一种是生命上的创造,如何丰富和还原自己的人生,叫“成己”。他说,“生命的本性在于奋进向上”,又说,“人心正是宇宙生命本原的最大透露而已”。“人之所以为人在其心”。即,以心主宰身,才能争取主动的人生。
梁漱溟长子梁培宽已退休20年。他一心整理父亲梁漱溟的文字,编辑出版了厚厚8卷本的《梁漱溟全集》和几十种单行本。但他是学生物专业的,开始时对父亲的东西实在不懂,只是硬着头皮去做。“1982年,我联系出版他的第一本书《人心与人生》时,出版社提出两个条件:一是可以出版,但不能公开出售;二是只印2000册,不能多印……20多年过去,世易时移,父亲的作品最终被认为是文化经典。”其次子梁培恕致力于撰写父亲的传记,前后历时20年。
梁培宽回忆,1918年,父亲曾倡议在北京大学组织一个孔子研究会,这个时间可以作为父亲思想转变的一个标志。“他有一种醒悟——现实的生活和他自己的佛学观、人生观有矛盾。佛学是出世的,而他所面对的是世上纷繁事。这中间是有冲突的。”“他觉得,他必须把力量集中到一头去,最后他就归结为‘儒’。佛学之道,是放下了,但不是放弃。”
1986年,梁培恕为了摒除外界对父亲的误解,自己动笔撰写第一本父亲的传记——《中国最后一个大儒:记父亲梁漱溟》,前后历时20年。目前已写完父亲的第二本传记——《架桥人和他的梦》。父亲的第三本传记《人类需要认识自己》也即将动笔。梁培恕称自己这二十多年来大概就只做了这么一件事,就是在解读父亲。
梁培恕对父亲的学术思想这样理解:“父亲曾说过,西方文化是向外用力的文化,而中国文化是向内用力的文化。因此,东方文化是心的文化,西方文化是身的文化。中国人向内用力的结果,是对心有很多修养方面的要求,西方文章认识人本,其科学对于人的外围世界研究透彻——如果两种文化不能够融合,就会出现很大的偏差。”梁漱溟深感东西方文化沟通的重要性。在他所创造的文化里,如何使二者更好地结合起来为人类所用,便是人类认识自己所必修的功课。
他记忆里的父亲经常说的一句话是“表里如一、独立思考”。“如果说他的性格中有一点重要的东西,那就是‘甘于清贫,安于现世的生活’。”梁培恕说。
“文革”初抄家时,开始写《人心与人生》
梁漱溟的人生哲学带有鲜明的理想主义色彩,这也是他后来“出世”信佛的重要原因。张中行曾这样赞誉梁漱溟的风骨:“梁先生可敬之处不少:有悲天悯人之怀,一也。 忠于理想,碰钉子不退,二也。 直,有一句,说一句,心口如一,三也。 受大而重之力压,不低头,为士林保存一点点元气,四也。不做歌颂八股,阿谀奉承,以换取驽驾的享受,五也。”
这样一个大儒,在“文革”中的生活状态和精神状态怎样?
梁培宽回忆说,父亲在“文革”冲击中,心理的承受能力很强。最开始抄家时,他竟开始写《人心与人生》。这也就是在“文革”刚刚开始以后一个月——外界的风云动荡没有颠覆他内心的奠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