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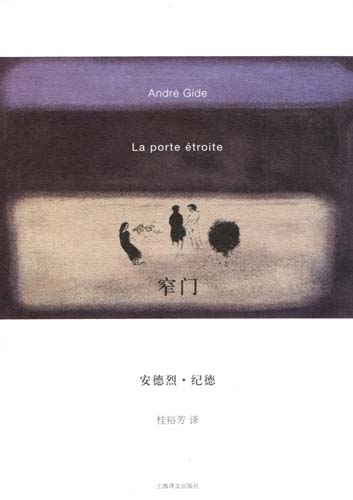 法国人究竟还是从骨子里反圆满的,他们的浪漫包括了浓烈之爱,亦将迂回试探前前后后的狼狈与暧昧收入囊中,在纪德笔下,则又载上一重贯穿生命的信仰之愁,与情感百战纠结,不死不休。 法国人究竟还是从骨子里反圆满的,他们的浪漫包括了浓烈之爱,亦将迂回试探前前后后的狼狈与暧昧收入囊中,在纪德笔下,则又载上一重贯穿生命的信仰之愁,与情感百战纠结,不死不休。
《窄门》里的阿莉莎,便是一个恪守神道而压抑住内心挚诚真情的典型,面对青梅竹马的表弟热罗姆,数次接受了寂寞的邀请而又随即妆上矜持粉饰,一封封写满了爱的书信寄往热罗姆来信的每一处异乡,却在每一次见面时沉默。由春到夏,由秋到冬,日子一年年,她的母亲背叛了家庭跟人跑了;她的父亲日渐苍老;她的妹妹爱上了热罗姆却没能得到她苦心成全的幸福、还是嫁了别人;妹妹生了孩子;父亲死了;她已然撤下所有与热罗姆从小到大的爱恋痕迹:刻意梳了头、搬走了所有曾与热罗姆一同读过的书、冷冷地面对每一次到来都成熟一点也爱她更深的热罗姆。最后一次等到了热罗姆来到房前,她“掏出一个用纸裹着的小包”,包里是热罗姆最喜欢的那个紫晶十字架,她没有能成功说服热罗姆收下,却真个在不久后,永远离开了世界、离开了他。
纪德选择这枚十字架结束最后一次见面,无疑是将贯穿小说的宗教“纸枷锁”固化成一件具体物件,让阿莉莎圣洁的理想国沉落地面,变成现实悲剧的一部分。阿莉莎的所有沉默不语与信中停不了的爱爱爱,都是压抑与反叛的激烈焦灼。《窄门》全篇大部分取的是热罗姆的视角,以热罗姆的第一人称出发,不紧不慢叙述着他们的童年、家族、爱恋,然而真正推进情节的反倒是经由热罗姆之口叙述的一封封来信以及最后阿莉莎的日记。如果说透过少年的热罗姆的眼光,在教堂里听伏蒂埃牧师念着“你们要努力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时一动不动地看着坐在他前排几个座位的阿莉莎的侧影是他们命定悲剧的开端,那么日后的年月,无论是阿莉莎为了成全妹妹朱莉埃特而压抑自己,还是与热罗姆约定“摘下脖子上紫晶十字架之日便是你我缘尽之时”,都是阿莉莎具体而坚毅地向着那道“引到永生”的窄门不懈践行着追求。她因为笃信“窄门”而一意追寻,又因热恋热罗姆而陷入苦境,最后她的所有言行成为将热罗姆推上窄门的自我毁亡。
理智与情感,终于还是情感占了上风。这般禁制原是求永生之所为,而目的却是为了爱人得永生。
纵观纪德其他代表作如《背德者》或《伪币制造者》,写的都是孤立入世的挣脱,挣脱家庭,挣脱旧观念,挣脱道德枷锁,而《窄门》则尽情描绘着一位黛玉式备受煎熬郁郁而终的幽怨闺秀,体现在阿莉莎身上的将爱未爱与对圣境的向往,似乎都在证明:这一次,叛逆的名字叫做孤独。但其实不然,阿莉莎的性格与纠缠在她心上的丝丝缕缕,恰是纪德本人的精神自画像,作为深受新教道德观束缚的青年纪德来说,叛逆固然是一种表达,而关于叛逆本身,也是他斗争的一部分,在阿莉莎的求索人生里,初时是为教义而舍弃爱情,到后来竟是为爱人得教义而舍弃自我,又回到了原点,此时的爱与束缚纠缠不清,她的选择基点仍是爱。而纪德之叛逆,要叛的也不仅仅是年少幽闭的本身,而是整个对生命的态度,选择燃尽年华,本身是最大的离经叛道。
《窄门》篇幅并不长,读得却十分缓慢,通篇的故事颇有《花样年华》的味道,却多了不少命运的惨烈,这惨烈深深埋藏在风平浪静的叙事之下。忽然想起,当年《花样年华》的原声碟,出版了双碟版、完整收录了梅林茂作曲的全部音乐素材的,正是情圣法国人,而戛纳电影节对梁朝伟演技的肯定,无疑也表现出一点浪漫国民对这种进队拉锯终不得的潜在内心趣味。而作为安德烈·纪德人到中年却是创作黄金期刚刚开始的阶段,《窄门》无疑继承并变相发扬了《背德者》的反思因子,也借此埋下了日后一系列纪德式“流浪“或”离经叛道“的伏笔。这也许不是他最好的作品,却一语道破天机:“入天堂的门,窄得容不下两个人”,而且,就算剩下一个人,他也绝对不想再得永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