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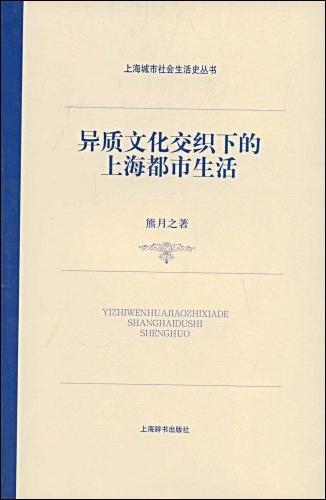 说起老上海——近代兴起的中国第一大商埠、被誉为“东方的巴黎”,总是给我们光怪陆离、灯红酒绿的印象。这就是历史给我们留下的记忆?在这光怪陆离、灯红酒绿的背后,这个特殊区域的社会本质又是什么?她展现了中国文化的哪个面?在近代中国开始走向世界、社会转型过程中,老上海又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说起老上海——近代兴起的中国第一大商埠、被誉为“东方的巴黎”,总是给我们光怪陆离、灯红酒绿的印象。这就是历史给我们留下的记忆?在这光怪陆离、灯红酒绿的背后,这个特殊区域的社会本质又是什么?她展现了中国文化的哪个面?在近代中国开始走向世界、社会转型过程中,老上海又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熊月之《异质文化交织下的上海都市生活》一书,以及该书所系的“上海城市社会生活史丛书”系列(第一批12本,上海辞书出版社2008年版;第二批14本,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版),就给我们展示了近代上海种种有别于其他地方的特异风貌,使我们看到了一个与我们历史记忆的近代中国形象判然不同的“另一个形象”,——一个多元空间和多元性格的中国都市。
中国古来自成天下,虽时有纷争并立,但华夏文明一统天下是常态,由此形成了华夏中心的文明传统。时至晚清,西方列强破门而入,通商口岸大门洞开,西方势力如滚滚洪流汹涌而来,华夏文明的一统天下被打破,中西文明的冲撞与交汇成为必然。与外来文明如何交汇,结果如何?决定着中国的未来,也考验着中华文明的适应能力与生存能力。这种文明的冲撞与交汇,呈现着种种不同形态,代表着中华文明发生的不同反应与变异。首当其冲的通商巨埠——上海,就呈现了一幅殖民阴影下多元文化交织的奇异景观,展现了中华文明的一种变异形态,也铸造了上海人特有的文化性格。
近代上海是一个多元文明交织并存的空间。这里有三个区域:老城区、英美租界(1863年合并,后称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各区分属不同的机构管理,因而有不同的市政体系、司法机构,不同的税收制度和卫生规则,甚至不同规格的道路车轨。在这不同的区域里,混居着来自西洋东洋、全国各地、四面八方的各色居民。漂洋过海而来的外国人,被中国人统称为“洋人”。但这些洋人却是来自世界不同国家与各个角落。自开埠直至新中国成立前的百年时间里,在上海的外侨人口最多时超过15万,所属国籍和民族最多时超过60个,其中人数最多的是英、美、法、德、日、俄等国人,其他最多时超过百人的还有印度、澳大利亚、朝鲜、越南、葡萄牙、意大利、波兰、希腊、捷克、西班牙、丹麦、瑞士、挪威、荷兰、瑞典、乌拉圭等,计有二十几个国家。这么多国家的各类侨民聚居在这方寸之地,真可说是个小世界了。当然这里为数最多的居民还是本土的华人,以数十万、成百万计,他们也大多是外地来的移民,来自全国各地东西南北,尤以周边和沿海的江、浙、闽、粤等地为多。洋人群体与华人群体之间,既有殖民性带来的歧视与怨恨,也有同居共处的交往与合作,彼此维持着交错复杂的关系。
这些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混居于一处的中外移民,长着不同的肤色和相貌,穿着不同的服装,说着不同的国语方言,他们也带来了各自不同的文明风俗和生活方式。因而这里有不同的建筑房屋、不同的生活用具、不同的货币,不同的宗教、不同的娱乐场所、不同的休闲活动、不同的节日庆典、不同的礼仪习惯、不同风味的餐馆酒楼、不同腔调的戏剧乐曲……,总之,举凡衣食住行、用度玩乐等生活事项,几乎无不多样并存。
来自各省各地、生活在如此多元多样的生活空间里的中国人,要在这个新环境里寻求生存,就不得不适应和改变,由此形成了独特的文化性格。他们具有开放性与包容性,对任何新事物见多不怪,宽容待之,也易于接受。如在晚清时期举国斥洋货为“奇技淫巧”耻于购用,上海人则最早流行使用洋货,而且喜新代旧、花样多、流行快,形成求新求洋为流行时尚的传统。上海人务实而善于学习,开埠不久就风行学习外语,在内地士大夫标榜“华夷之辨”、群起反对同文馆招士人学习西学之时,上海则沿街开设西语学塾,还创造出了以上海土话模仿英语发音、简便易学的“洋泾浜英语”,成为商街店伙通用的商务用语。与此同时,上海人对西洋有更多的憧憬与向往,崇洋鄙土、喜新厌旧、趋时追风,视外地为“乡下”,鄙华风为“土气”,又缺少了些本土的认同与根基。
近代上海又是一个多元权力边缘交错的缝隙地带。中国官府控制老城区,但对租界则没有直接管理权,租界里的华人居民虽生活在本土,却不受中国官府管理。英美租界与法租界则分别由英、美、法国人及外侨代表组成市政机构进行管理,华人长期不得参与。因而这里的市政管理以维护外侨利益为准则,很少顾及华人利益。华人居民在这种中外权力控制的缝隙中,处于散漫自治的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