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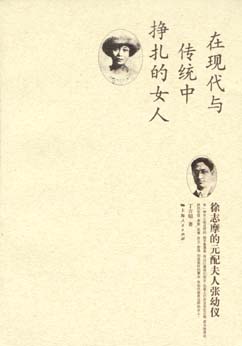 古希腊的阿里斯托芬曾在众人举杯会饮之时讲了一个关于人类性别划分的故事,故事中所谓“最初的人”即原人是球形的,分为男人、女人和阴阳人(即兼具男女两种性别的人),后被宙斯用手中的霹雳劈成了两半,成为今天的男人、女人。因此,今天的人一生下来就被赋予了一个任务,即是寻找自己的另一半,以恢复自己完满的全人形象。这本是当日那些宴席上的哲人们关于爱情话题的一个引子,蕴含着无数种诠释的可能性,可它亦可以被当成此刻我叙述中的一个女人一生的一个注脚,因为她正是通过这种缺失中的找寻返回了她自身。 古希腊的阿里斯托芬曾在众人举杯会饮之时讲了一个关于人类性别划分的故事,故事中所谓“最初的人”即原人是球形的,分为男人、女人和阴阳人(即兼具男女两种性别的人),后被宙斯用手中的霹雳劈成了两半,成为今天的男人、女人。因此,今天的人一生下来就被赋予了一个任务,即是寻找自己的另一半,以恢复自己完满的全人形象。这本是当日那些宴席上的哲人们关于爱情话题的一个引子,蕴含着无数种诠释的可能性,可它亦可以被当成此刻我叙述中的一个女人一生的一个注脚,因为她正是通过这种缺失中的找寻返回了她自身。
这是一个被神话包裹着的时代,女人除了被各种创世的神话所包裹,更是被那些由男性所亲手创造出的关于她们的神话所围绕。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被以男性为主导的社会创造出来的,这里的“女人”意指的是处于第二性的主体特征。在西蒙娜·德·波伏娃的《第二性》中,这一惊人的预言无疑也有着对男性笔下那些无论是刻毒或是满含赞誉的“女性神话”的质疑,即使放到今天恐怕也并不过时。张幼仪就出生在这样一个女性处于被忽视、被支配的时代,而她出生时的中国,在历史坐标上又占据着一个特殊的位置:那些被称为是摩登的幼芽正逐渐从那些传统的软肋处生发出来。摩登这个词之所以比直译为现代更好就在于较之于现代性本体,摩登则更像是影子般仅浅显地作用于事物的表面。不仅仅是张幼仪和无数像她一样的女性,当时整个中国(当然也包括男性)都处在这样一个摩登却又暧昧不清,充满了种种变数的时代。张幼仪的特殊从一开始就和她所出生的家庭、时代休戚相关,如果不是她那个显赫的家庭,两个曾在那个时代即使不是呼风唤雨却也闻名政商两界的哥哥,她也不会与同样出生名门的倜傥才子徐志摩结下一段看似不幸却也相互成就的姻缘。
在以徐志摩为主角的传记中,其原配夫人张幼仪仅能占到那么薄薄几页,一是他们二人间来往的书信不多,且很多并没有公诸于世;二来恐怕还是作传者也并没有将张幼仪看作是徐志摩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柏拉图曾经说过:个体在另一个人身上寻找的,不是他自己的另一半,而是与他的灵魂结合在一起的真理。徐志摩在张幼仪身上(起码据他所称)并没有找到他所需要的真理。比起他为林徽因创作的无数感人书信及诗篇和传世甚广的《爱眉小札》,张幼仪被一篇她自己都未曾看到过的《笑解烦恼结》就打发了,看来她的确不是徐志摩内心中所执着追求、甚至连生命也在所不惜的“真理”。曾以一篇《论中国妇女之地位》获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学位的徐志摩,为着这爱的真理就这么离开了身处异乡尚有身孕的妻子。那些围绕存在紧密相连的部分被抽象而富于感召力的“形而上”无情地敲去了。这场被称之为近代中国“第一桩离婚案件”也因其丰富的象征意义而几乎成为了那个时代的又一个关于男女爱情、婚姻的隐喻:即使是同情女人,抱着解放女人,呼唤新女性出现的男人也同样用另一种名教使女性深陷另一层囹圄,女性现实境遇中的苦难却丝毫未为之减轻。罗素恐怕没有想到是自己与徐志摩探讨的一套关于追求自由爱情的理论使诗人下定了“休妻”的决心,而这样的行为的合理性也因着这“真理”的第一性而不再顾及一个女人现实中糟糕的处境。徐志摩是带着解放妻子于封建婚姻的雄心来离婚的,殊不知这桩婚姻中的妻子张幼仪并不希望被“解放”,那些所谓束缚她的传统伦理价值观恰恰是她追求自己心中贤妻良母理想的基础。正是这理想与现实的反讽使得这次婚姻成了近代中国历史上具有标志性、代表性的事件。可以说,没有林徽因,徐志摩迟早仍会踏出与原配妻子离婚这一步,但如果他没有出国,恐怕他还真不会和张幼仪离婚,徐的出国的确如本书作者丁言昭所说,是张幼仪人生中的一次转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