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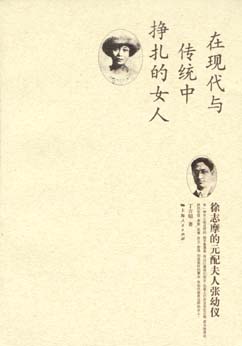 热闹的婚礼 热闹的婚礼
1915年12月5日(阴历十月二十九),徐志摩和张幼仪在硖石商会举行婚礼,由萧山汤蛰先生当证婚人。
这天早上,张幼仪用过早饭后,就由堂姐帮她化新娘妆。因为徐志摩提出要一个新式的新娘,所以那天,张幼仪穿了件非常华丽的粉红色婚礼服,里面有好多层丝裙,最外面的一层裙子上绣了几条龙。头上戴了顶凤冠。看上去,既是西洋式的又带点儿中国传统的风格。
母亲和堂姐帮张幼仪穿戴好以后,又仔细地检查了一遍,确信没有漏掉什么,才领着张幼仪下楼去。张幼仪看见父亲、哥哥、姐姐们都穿着礼服在门外等着,在张幼仪准备上轿的那一刻,母亲把她头巾放下来,张幼仪只觉得眼前一片漆黑,什么也看不见,心里好紧张,身体差点失去平衡。旁边有几只有力的手抓住她的胳臂,她这才站稳,在众人的帮助下,张幼仪坐进了花轿。就听到母亲的声音:“别害怕,有人会一直扶着你的。”
这时,鞭炮声响起、乐队奏起了乐曲,哭新娘声也此起彼伏地响起,好不热闹!队伍出发了,最前面的有4个人,两个举着张家的旗,两个举着徐家的旗,随后就是张幼仪的轿子,哥哥走在轿子的旁边,然后是张家女眷的轿子,最后是撑着红伞的乐队。徐家的队伍紧跟在他们的后面。终于,他们到了礼堂。
礼堂里聚集了好几百嘉宾,张幼仪戴着笨重的头冠,好不容易被人搀扶着走出轿子,进了礼堂。由于时间长了张幼仪逐渐能看见外面的人影了。她被人领着走过一排排的客人,最后走到一张桌子前停住。这时,她听见隔壁有人紧张地清了清嗓子,她知道这肯定是徐志摩。“原来他和我一样紧张。”张幼仪想着,不觉有点放宽了心。
接下去,他们拜了天地,又拜了高堂,还要向七大姑、八大姨以及客人们磕头,只见徐志摩和张幼仪跪下、站起,站起、又跪下,不知磕了多少头,下了多少跪,总之,他俩过了一个多星期,膝盖还在痛,路都没法走。
当徐志摩掀起她的头盖时,张幼仪的心开始发抖,她又是期待又是害怕。她期待他的目光,可是又害怕迎接他的目光,她之前只在楼上偷偷地瞅过他一次,幸亏,她戴的头冠太重,使她无法抬起头直视他的眼睛,仅仅看到他那尖下巴颏儿。
在闹新房时,张幼仪牢牢地记住母亲和堂姐的话,不管别人怎么闹、怎么吵,她始终一声不吭地坐在那里。在闹新房这天,不分老小,不分辈分,谁都可以与新郎新娘开任何玩笑。众人大约闹到后半夜才散去。
这一夜,徐志摩没有进洞房,而是躲到奶奶的屋里睡了一夜。以后,由于大人的督促,徐志摩才在佣人的簇拥下,进了新房。他们没有说话。从此,沉默就没有离开过他们。
婚后的寂寞
徐志摩回来结婚后,依父亲的意思,他应该参与管理徐家的一些工厂、作坊,可是徐志摩对这些毫无兴趣,整天捧着书,心里觉得空荡荡的。有时,他会对张幼仪说些在杭州一中和北京大学读预科时的事,徐志摩说的时候,那种兴奋、那种愉快、那种留恋,使张幼仪很感动。她问徐志摩:“既然那么好,为什么你现在不再去读书呢?”一句话,问得徐志摩一时语塞,说不出话来。
张幼仪看看徐志摩,温柔地说:“你不用着急,我来替你想办法。”张幼仪是个聪明人,她想到了二哥张君劢。让二哥介绍徐志摩进学校读书,公公大概不会反对吧!?
浸信会是基督教新教宗派之一,是美国人在上海办的教会学校。徐申如对于张君劢介绍的这个学校,非常满意。首先上海离硖石比较近,坐火车一个小时就能够到达,儿子在星期天便可以回来,与新婚妻子团聚,他也能经常看到儿子。徐志摩读了一年不到,即北上,考入天津的北洋大学法科。
徐志摩对朋友热情有加,对自己的妻子却是冷淡无比。早在结婚之前,徐志摩第一次见到张幼仪的照片时,把嘴往下一撇,用充满鄙夷的口气说道:“乡下土包子!”自从张幼仪嫁到徐家,徐志摩从来没有正眼看过她,就好像她不存在一样。
张幼仪在空空的屋子里,心里也是空空的。
徐志摩出国留学
儿子阿欢100天的时候,徐志摩从北京回到硖石。他看到活泼可爱的儿子时,心里非常高兴,他当爸爸了!可是他又有一丝担忧,如果将来儿子向着母亲,而不向着他,他该怎么办呢?
张幼仪与徐志摩结婚几载,可是两人真正待在一起的时间大约只有几个月,互相之间并不太了解。但有一点,张幼仪特别清楚,丈夫喜欢爱读书的女人,这与张幼仪的本意是相符合的。婚后不久,张幼仪曾经写信给苏州第二女子师范学校,希望能进学校读完中断的学业。校方认为张幼仪必须重新读一年,也就是说,张幼仪得读两年才能毕业。两年,对张幼仪来说,实在太长了,因为一个新媳妇离开公婆这么多时间,于情理上也讲不过去啊!于是她放弃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