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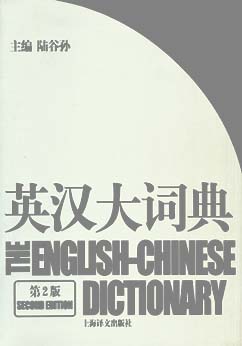 已经完成事业转企业改制的上海世纪出版集团,近日成立三大编纂处——《辞海》编纂处、《汉语大词典》编纂处、《英汉大词典》编纂处。“稀奇”的是:三大编纂处均为事业编制,属于“吃皇粮”的单位。由此,很多人看不懂:一会儿这样改,一会儿那样改,文化到底要走哪条路?记者在深入采访后发现,在三大编纂处成立的背后,其实有一个不能不思考和提出的问题:今后谁来编纂词典? 已经完成事业转企业改制的上海世纪出版集团,近日成立三大编纂处——《辞海》编纂处、《汉语大词典》编纂处、《英汉大词典》编纂处。“稀奇”的是:三大编纂处均为事业编制,属于“吃皇粮”的单位。由此,很多人看不懂:一会儿这样改,一会儿那样改,文化到底要走哪条路?记者在深入采访后发现,在三大编纂处成立的背后,其实有一个不能不思考和提出的问题:今后谁来编纂词典?
《辞海》最初编纂于1915年,1936年出版。1957年着手修订,1979年出版修订版。《汉语大词典》《英汉大词典》始编于1975年。1986年,《汉语大词典》首卷编成,1994年全部12卷出版。《英汉大词典》于1989年完成上卷,2年后下卷编纂出版。
从编写到出版,三大词典经历了10多年、甚至20多年的漫长时间。编写人员由黑发到白发,有些人甚至累倒在编写岗位上,未曾见到书稿出版的这一天。成百上千的全国各地专家、学者,参与了编纂工作,甚至放弃了出国、出书、升职等机会。从中央到地方政府,全力支持三大词典的编纂。
一部《辞海》,从着手修订到一版再版,凝聚了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三代领导人的关心。中央军委、外交部、中组部、中宣部、国家民委、国务院侨办等中央各部门,组织力量审定书稿。《汉语大词典》和《英汉大词典》,是周恩来总理重病期间,签发国务院令后编写的。江苏、浙江、安徽、山东、福建、上海的1000多名语文工作者,参加了《汉语大词典》的编写。在编纂的16年中,《英汉大词典》有7名工作人员不幸逝世。1991年6月,离出版只有3个月,46岁的女编辑乔艾宓倒在工作岗位上。在她的遗体前,主编陆谷孙悲情地说:“在一位日复一日一起工作的同仁突然离去之际,惊愕和悲痛会升华我们的情怀,启发我们对生与死作深沉的哲学思考。思考的同时,我们一方面会变得更恬淡于名利,更为宽容。另一方面会对我们共同的事业,加深一种带有神圣意味的使命感,变得更为执著和勇敢。”
然而,今天在文化界谈及这三部大词典时,很多人不是兴奋,而是有一种侥幸。他们说:“幸亏这几部大书,编纂得早。如果放在今天,肯定编纂不了。恐怕以后,也不会编纂成功。”
难道是九斤老太“今不如昔”论调的复燃?非也。由于《辞海》、《汉语大词典》的编纂,上海“延伸”出辞书出版社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除两部大型词典外,两社每年还出版其它书籍六七百种。《英汉大词典》则属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三家出版单位,在改制后都成为自负盈亏的企业单位。以一家出版社之力,承担如此重大的编纂出版工作,存在许多困难:一是资金。即便是修订,三大词典的投资仍非常大。刚修订出版的《英汉大词典》,首印15000部,全部卖完,也收回不了前期投资的钱。从2001年起,在《辞海》基础上,上海辞书出版社承担了《大辞海》的编纂出版任务。这部词典共38卷,篇幅是《辞海》的三倍。目前,《大辞海》已出版了10个分卷。但是,每出版一卷,出版社就要赔上40万元钱。二是编写力量。为确保大型工具书的权威性、科学性,主编和各分科主编及主要撰写者,都需要一流专家主持。为此,舒新城、陈望道、刘大杰、苏步青、王力、叶圣陶、陈原、陈瀚伯、夏征农、陆谷孙、吴莹等全国著名学者,都曾通过行政手段,参与三大词典的编纂工作。今天,以一家出版社之力,哪能调用全国的力量?三是名与利。一条词目,看起来几十、几百个字,但是往往需要编纂者熟知一个领域,熟读几十、几百本书。撰写一个条目,也就几十元的报酬。比起今天,一场几千元甚至更高报酬的讲座,太没有吸引力了。无名又无利,谁来守住清贫和寂寞?
显然,问题的提出,并不是危言耸听。谁来编纂词典?这是一个迫切需要解答的问题。今日之图书市场,各种词典书籍也不算少。但是仔细看看,大多是拼拼凑凑抄袭而来,错误百出。一些双语词典,多是据国外词典翻译而来。由此,意识形态主导权、知识产权等一系列问题又被提上议事日程。
《英汉大词典》出版后,在国内外获得很好口碑。一部由中国人自己编纂的双语词典,是一个国家或民族在对外开放和国际交流中,保持语言文化独立性和纯洁性的需要。联合国前首席英语翻译斯蒂芬·培尔说:“《英汉大词典》是一部规范的词典。像‘发展是硬道理’等词,我们都要从这本词典中去查找。”《辞海》,仍是我国目前唯一一部大型综合性辞典。《汉语大词典》集古今汉语之大成。在世界上,这些权威性工具书,代表着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文化,一般都被看作是国家荣誉和民族自立的象征。从这个意义上说,在辞书界,一切抄袭、拼凑之作,损害的不仅是读者利益,还有国家形象。
谁来编纂词典?需要文化人的奉献,需要出版人的眼光,需要国家对文化的重视。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在这样的时刻,成立三大编纂处,以事业单位性质独立开展工作,也许是一条上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