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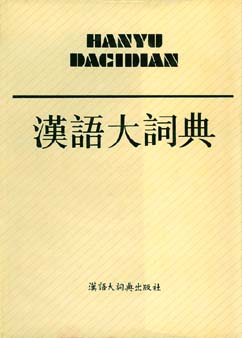 1975年5月,国家出版局和教育部在广州召开会议,讨论中外语文词典编写和出版的十年规划。当年8月21日,经周总理批准,国务院转发了《关于中外语文词典编写出版规划座谈会的报告》(即国发137号文件),要求出版界组织力量编写出版160部大小语文词典。其中规模最大的《汉语大词典》,商定由上海、江苏、浙江、山东、福建、安徽等五省一市合作编纂。回顾《汉语大词典》的出版历程,身为这项工作的早期亲历者,我体会至深。 1975年5月,国家出版局和教育部在广州召开会议,讨论中外语文词典编写和出版的十年规划。当年8月21日,经周总理批准,国务院转发了《关于中外语文词典编写出版规划座谈会的报告》(即国发137号文件),要求出版界组织力量编写出版160部大小语文词典。其中规模最大的《汉语大词典》,商定由上海、江苏、浙江、山东、福建、安徽等五省一市合作编纂。回顾《汉语大词典》的出版历程,身为这项工作的早期亲历者,我体会至深。
当时,国家出版局会同教育部成立了“中外语文词典编写领导小组”,并在国家出版局设办公室。在五省一市,同样在政府建立“领导小组”,在出版局设办公室(即后来的省市“词办”),并委托上海负责总集成的工作。随后华东五省一市“词办”,立即聚会商议开展编写工作的步骤。
那时候“四人帮”还没倒台,那股违背词典知识性的规律、要把词典编成政治教科书的极左思潮依然存在;很多语文教师还散落赋闲,组织编写队伍,困难重重。但编纂一部最新最全的《汉语大词典》,无疑具有重大价值和紧迫意义。国家出版局陈翰伯局长有一次说过这样的话:“日本有一部《大汉和词典》,台湾出了一部《中文大词典》,而我们没有,实在脸上无光。”
不仅要编,还必须编出高水平。当时对这部词典的定位是,坚持高起点、高标准,要准确反映汉语源流发展的演变,纠正以往某些汉语词书中存在的误导,在收词、书证、释义、体例、检索等各方面,充分体现出科学性和权威性,在学术上超过台湾和日本的同类词典。大家认识到,这是一项国家重大文化工程,是传承和弘扬中华文化的重要基本建设,务必下最大决心,全力以赴。
有了上述共识,立即制订实施方案,着手物色人选,组建编写队伍。1976年夏天,在上海衡山饭店召开了《汉语大词典》首次编写工作会议,五省一市的编写人员基本上都参加了。这次会议重申了137号文件精神,明确了词典性质、编写方针和选词阶段的工作要求,确立了高起点、高标准的编纂指导思想。
按汉字字头分工承担了各自的编写任务之后,五省一市陆续组建起不同形式的编写机构。有的省将教师抽调在一起,建立集中的编写组,也有的省则在有条件的地市,建立分散的编写组,如江苏省就建立了10个编写组。五省一市前后参与这部大词典编写工作的,涉及43个单位的四百余人。
有人曾经有过这样的疑虑:编词典是复杂细活,通常都是由少数专家集中编纂,现在《汉语大词典》动员这么多人,又是分散来编,其质量如何保证。对此五省一市负责编写的人士认为,新编《汉语大词典》,容量大,标准高,在刚刚经历了“文革”浩劫、文教战线尚处拨乱反正之际,想用传统编词典的办法来编,那简直是不可能的。从现实环境出发,只能采取大协作的方式。这样做虽出于因时制宜的一次尝试,但只要加强领导,精心组织,工作做细,对大协作的全过程扬长避短,也许可以探索出合力编词典的另一种新思路。
“领导小组”做出决策,五省一市必须统一执行,不许走样,没有例外。充分发挥上海“词办”的协调功能。上海“词办”起初由束韧秋、孙厚璞担任正副主任,没多久改由孙厚璞任主任,共事的还有郑拾风、金文明等人,他们对五省一市的编写工作,发挥了很好的协调与指导作用。后来上海“词办”扩展为《汉语大词典》编纂处,由王涛负责,工作也很有成效。
制订统一的编写工作规则是保证大协作不会走样的重要措施。编写人员在领会词典性质、编写方针、编写体例、质量保证等基本精神基础上,还必须吃透统一规定的收词原则、书证选择、准确释义、编辑体例、乃至标点符号等多方面的要求。在编写全过程特别强调,只有统一的规则,没有个人的风格。为了切实做到严谨、规范,上海“词办”还特意出版了一本《〈汉语大词典〉编写手册》,把大小各项要求具体书面化。正因为有了这样一套细化了的编写规则和保证措施,使整个编写工作没有出现“各吹各的调”。
有了规则,还必须辅以必要的沟通、交流和监督。五省一市除有各家“词办”的《编写工作通讯》经常交流情况以外,特别重视及时开会交流磋商。仅在早期选收词条阶段,几乎每年都要召开编写工作会议。先是1977年在青岛开,随后接连在黄山、苏州、杭州、厦门等地召开,这中间还开过多次小型的汇报会、论证会、专题讨论会。这些频繁的交流,有助于及时发现问题,统一认识,监督进度,促进了编写工作的“一盘棋”。
|